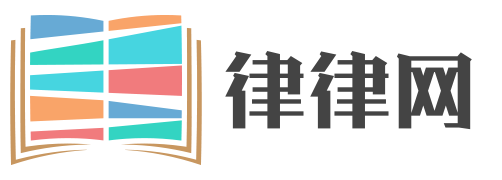信托业的激情年代——一个信托人的手记(上)
发布时间:2019-08-12 06:59:15
screen.width-55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50;">
(一)埋葬在历史的废墟下
screen.width-55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50;">
这次会议让我永世难忘。
当公司总经理语带哽咽地宣布,公司将正式关闭,清算组不日将进驻公司全面接管时,会场一片寂静。不知是谁突然放声哭泣,在场的公司百余名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热泪赢怀。虽然早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但它终于来临时我们仍然难于接受。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这个一年四季大多数日子艳阳高照的城市,天上的太阳却是血红的。记得上一次这样的痛快淋漓的哭泣是在1976年9月9日,那一天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黯然陨落,那一年我16岁。而今已跨入不惑之年的我,面对此情此景,却难于不惑。这不仅因为,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整整13年,从27岁到40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这个“单位”里度过,也不仅是因为我又要下岗,而这一次下岗是在年届被大多数单位拒之门外的年纪之际,更主要的是因为,从1995年8月开始,我们生存、生活的一切目的几乎就是为了避免今天这个结局。我们为使公司持续生存所付出的一切,这些年来支撑我们奋斗挣扎的理想、信念和雄心壮志,顷刻间都化为了乌有。
曾几何时,我们豪情万丈,认为自己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在创造着点石成金的神话,在肩负着力挽狂澜的使命。但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象狂奔不止的骑士唐吉珂德,当信托公司宣布关门,我们终于有时间仔细端详过去的时侯,才发现我们一直是在与风车战斗,充其量我们是被金融经济变革的大潮裹挟着东奔西走,左冲右突,随波逐流。十几年的时间只是历史的一刹那,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对于中国的金融和经济改革,中国信托业的历史却显得格外凝重。
当我们终于可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曾为之将最美好的青春年代予以奉献的信托公司,却多已经被埋葬在历史的废墟之下,毫无疑问,传统信托业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成为了改革的祭献。在中国,这或许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但没有什么会比这个结局更让人感慨万千,没有什么会比这个结局更让我们心痛万分。
(二)激情燃烧
screen.width-55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50;">
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似乎为所有的有志之士提供着万千机遇和广阔舞台。多个经济特区先后宣布建立,沿海十四个城市全面开放,那真的是一个沸腾的年代!中国的特区大多选在传统行政体制控制力较为薄弱的边远地区,而许多沿海开放城市也是经济并不发达甚至很落后的城市。或许正因为如此,特区和南方的沿海开放城市才为满怀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更好的舞台。
仍然清楚地记得1988年3月的一天,当我辞职南下穿越珠江三角洲的时候,珠三角的繁华、发达强烈地震撼了我,让我真正知道了中国的南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当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终于踏上特区的土地时,特区土地的荒芜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我。
从现在看来,这边远的蛮荒之地并不具备任何一种成为特区的基本条件。而在当时,在很短的期限内我们将成就一番改天换地的伟业的信念,我却从没有怀疑过。阿基米得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而在我们看来,把金子种在特区的土地上,高楼大厦就会象庄稼一样拔地而起,而我们手里拥有点石成金的工具---信托投资公司,因此我们就有了撬动地球的支点。
但是在这个无论是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缘条件都实在太脆弱的特区,最终我们才发现,这实在是一个梦想。虽然我们在地产泡沫崩溃之后,也曾作过艰难的挣扎,并将业务伸向内地和其他诸如证券之类的新生领域,但无奈特区的资源实在过于贫瘠,最终我们才崩溃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实际上,有些特区之所以得以避免我们的命运,甚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只不过反证了产业基础和历史积淀的重要,从根本上说,金融无法脱离产业基础而单独繁荣。
但是在中国经济改革于1979年启动的时候,在计划体制之外的具有市场调节因素的一切办法都被寄以了突破计划经济堡垒的厚望。当时中国所谓的金融业实际上也就是单一的银行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坚固堡垒。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可能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步,更不可能率先市场化,这与金融业的特殊敏感性有关,也与中国传统体制所具有的强大惯性有关。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994年之前,中国金融改革采取了与其他领域一样的所谓双轨制模式,而中国的信托业就是当时并存于传统金融体制之外的最大一根“轨道”。
虽然从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始,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信托业历经了五次重大整顿,并最终在1999年3月后被彻底推倒重来,但在1980年代,信托业无疑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先突破的领域和最“繁荣”的领域。换言之,信托业当时正是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最大的“特区”。和地理区域上的特区相叠加,特区的信托业当然就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这种特殊的土壤,造就了特区信托业空前绝后的繁荣,也造就了我们的梦想,造就了我们的光荣,但最后也造就了信托业自身及我们自己的灾难与悲剧。
在信托业的全盛时期,小小一个特区的信托公司竟然多达到二十余家,足以让其他所有的省区和直辖市都瞠呼其后。有人说那时特区的信托业就是金融业,金融业也即是信托业。信托业当时在特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当时满目荒芜的特区,除了特区的金字招牌、含金量甚高的财税优惠政策之外,最闪光的亮点大概就是相关部门特批的这些信托公司,这一条条连接着特区与内地、特区与海外的,为特区建设输送着大量资金的特殊管道。然而,如此之多的信托公司拥挤在这个缺乏产业基础,缺乏地缘经济优势的狭小区域内,其生存空间可想而知。
不过,当这里有了我们这批极富想象力和充满朝气、活力与激情的年轻人,奇迹的发生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当我几经曲折成为一家信托公司员工的时候,让我最为激动和难忘的是与我们同样年轻的总经理所说的一句,后来曾非常流行的话: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这是一家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来源于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几乎全部是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年轻企业。历史注定我们要从祖国各地聚会在这风云际会之地有一番作为,然后我们要有一番苦痛与最后挣扎,最终在信托业的丧礼中成为牺牲。于是,特区的可以炒作土地之“特”与信托业的大量融通资金的金融之“特”开始同时发挥作用,最终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圈地狂潮。而在事实上,在资金短时间内大量聚集但又没有任何其他资源可以依托的情况下,急于在最快的时间内以最简便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同时或许还被自己所描绘的特区美好前景所激动和陶醉,将脚下的土地做为下注的筹码,也可能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特区的发展几度风雨,堪称疯狂的大开发终于在1992年春天爆发。全国各地的热钱开始象潮水一样涌入特区,各金融机构营业部异常忙碌,柜台人员一度数钱数得手痛。最令人兴奋的是,地价飞涨,房价飞涨,套用炒股的话就是几乎每天一个涨停板。与此同时,特区的面貌也在日新月异,原先荒无人烟的新区主干道两旁,一幢幢高楼短短数月便拔地而起,正象春天里的庄稼一样。我们的“庄稼”也喜获丰收,公司办公室终于从原先一幢民房模样的小楼搬进了信托大厦顶层。
后来的统计表明,在那一时期,特区曾拥挤着中国超过20%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些房地产公司的背后,多具有银行、信托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背景,信托公司也理所当然地充当着主力军。更确切地说,是以特区内外的信托公司为主力军的金融机构,联手铸就了这个特区的恰若流星的辉煌,也同时造就了日后绵绵不断的痛楚。
(三)梦想终于破灭
screen.width-55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50;">
事实上,早在1993年6月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这个特区的正剧就已经落幕,而导演这场天方夜谭般辉煌神话的信托公司也由此盛极而衰,开始一步步走上其死亡之旅。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曾做过痛苦而拼死的挣扎,而且中间似乎几度回光返照,但置之死地后最终并没有象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故事那样出现逢凶化吉、皆大欢喜的终局。
这场由特区发端然后又迅速燃及整个南方沿海的地产狂热,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次金融崩溃,虽然这场金融危机最终被遏制在以南方沿海为主的不大的区域之内。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最先倒下的是中银国投---一个在海南和北海等地圈有数以平方公里计的大面积土地的大名鼎鼎的信托公司,然后是分支机构最多的中农信倒下,接着中创也跟着倒下;随后,海南的城市信用社支付危机全面爆发,把由几家信托公司拼凑起来的海南发展银行这个援救者拖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随着广国投宣布破产,各地信托投资公司就象多米洛骨牌一样纷纷倒下。最后,当大家都认为该倒下的已经全都倒下了,没有倒下的也就不会再倒之时,却出人意料地传来了财政部部属庞然大物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轰然倒地的巨响。在这个过程中,最先由信托公司引发的金融危机先后被传播到城乡信用社、小型商业银行,甚至五大银行的个别分支机构。而在区域上,先后蔓延波及海南、广东、广西、河南等数省。
从地产泡沫破灭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曾经率先引发圈地狂潮和造就过无数动人奇迹的特区,就开始越来越成为一个见证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遗迹,。特区许多人的思想至今仍然定格在1993年,难以承认特区已经被彻底边缘化的事实。就象海水退却之后露出海底的礁石,特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几乎都与地产泡沫破灭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只有那些历经十年风雨仍然孤独地踯立在空荡大街两边的黝黑的半拉子钢筋水泥建筑,还在向人们讲述着昔日特区的繁荣与辉煌。在今天,,被用于招揽游客。,树立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招牌,。
而我们这些曾经自认为创造了神话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至21世纪初年,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煎熬之后,不得不开始向其他地域流散。一部分人重新回归那个他们曾经厌恶甚至憎恨的体制,更多的人则是再次选择了浪迹天涯。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重庆,---,经常很容易地发现我周围陌生的面孔来自我曾激情燃烧的地方,他们几句话就会冒出特区的名字或者特区人特有的用语,他们已经离开特区但他们谈论最多的仍然是“特区”。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无论身在何地,都已经被深深打上特区的烙印。我们之所以逃离了特区,不仅因为那里燃尽了我们一生最为火热的激情,我们奋斗的结果却以悲剧终局,让那里成为我们的伤心之地,更因为在那个快速干涸的池子里,我们这类人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毕竟,象北大的才子陆某一样坐能行文、站能杀猪卖肉的能伸能曲的大丈夫并不是很多。
(四)制度之荒唐
其实,信托业的覆亡命运早在出生之时几乎就已经注定了。
到信托公司工作之后我才终于明白:所谓的信托公司,如果说与银行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的话,那就是银行在做的,我们信托几乎都做了;而银行没有做的,我们也做了。按照许多人的说法,信托公司除了信托业务没做之外,什么都做了,或者说除了该做的没有做之外,什么都做了。其中,信托公司开办的所谓“信托存款”业务与银行的存款业务并无本质不同。,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的条条框框,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尤其是在慌不择路、饥不择饲之时。不过信托公司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不是存款,而是同业拆入,主要是从四大专业银行及其所开办的资金市场拆借资金。在资金运用方面,可以分成“自营投资”和信贷业务两部分。后者与银行的信贷业务相比除了名称叫作“信托贷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自营投资”主要是通过下属子公司、孙公司介入工业、商业、服务、贸易、旅游、运输、房地产开发等产业投资,并在90年代开始转向证券投资。有的信托公司投资领域之杂、范围之广,开办的附属公司之多,连许多信托公司内部人士都难以搞清楚。
信托人士曾经最为骄傲、最爱说的就是:我们是金融百货公司,但恰恰忽略了无所不能其实与无能仅一步之遥。当某信托公司被关闭后清算出一家规模不小的养猪场时,该公司的员工都感到难于置信,血统高贵的信托公司竟然轻而易举地与蠢猪们成了一家。而这却是实实在的历史,是该信托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为了充分利用大片的闲置烂尾别墅,开办了这个规模不小的养猪场。信托公司的猪好歹也是住“别墅”长大的,由此似乎彰显出信托公司之尊贵,想必也是个值得炒作的卖点。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释然,甚至有些得意。
某信托人士每每在有各家银行人马同时在场的时候自嘲:,五大银行是‘正规军’,其他银行是‘土八路’,而咱信托就只好当‘土匪’了”。信托人其实早就明白自己不是好孩子,,、发出的指令几乎从来都是阳奉阴违;因为名叫信托公司却几乎从来不干也干不了真正的信托业务,就是干点信托的事情那也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高息揽存高息拆借同时也高息放贷,美其名曰高进高出。各信托公司为了筹钱不得不发明各种各样的融资工具:委托理财、国债回购、国债代保管单、国债再投资券、信托投资受益凭证等,以及通过超额发行获得批准的特种金融债券,用子公司的名义超规模发行企业债券等等,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如果说信托天生就是带着土匪和坏小孩的基因,那不得不问:信托公司的坏基因从何而来?不容忽视的是,信托公司的骨干成员和中高层领导,,为什么这么多“老革命”一到了信托就变成了坏小孩了呢?有人士这样认为,,路子也最野,并道出理由:其一,,但和“娘家”的许多在职干部们却是老朋友老伙计,;其二,,。这位人士总结说,最终是由屁股指挥脑袋,而不是脑袋指挥屁股。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及同行们所重复的不过是中国金融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再发生的故事:利用模糊的规则打擦边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乃至整个改革一直沿用的核心规则。当初在特区的信托业,许多人就是希望利用制度的模糊而乱中取胜,但不少人最终反被这种模糊规则所击倒。正象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的:在中国改革的词典中,特区的准确解释就是制度性模糊,它并不明确地告诉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只有语义模糊的政策暗示。在这样的模糊政策暗示中,只有精明人才能对这种暗示借题发挥。回过头来你才会发现,以前从来没有规定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最终你干的全都变成违规了。而到了干什么什么违规的时候,为了生存,你也就顾不上在乎什么是违规的了。
说到制度制定,今天的人会问为什么会有制度空白,为什么会有制度模糊,为什么不能有公平和清晰的规则。历史总是在不断进步,今天我们若再发出这样的疑问,与费解古代文明为何消失是一样的道理。当信托业于1979年重新恢复的时候,是在先有了多家信托公司之后,才有了一些模糊朦胧的制度,这些制度一开始几乎全部是一些“通知”、“纪要”“讲话”等,后来才出现了一些“办法”和“暂行条例”。而直到信托公司大规模关闭之时,尚无一个制度真正明确、准确、全面地为信托和信托业务下过定义。更确切地说,在《信托法》出台之前,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是信托。,包括利率管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法定准备金管理等。虽然这在今天一看就知道全是非信托业务的管理行为,但众多的信托公司就是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艰难地走完了它的历程。按照这样的制度,你若要发呆发傻非要做什么信托业务,那不喝西北风才怪。
信托业界的一些愤青,一说到信托公司历史上犯下的累累罪行就必言被逼无奈,露出一幅“良家妇女”的善良面孔和清纯的眼睛。客观、准确地说,并非是被逼无奈,因为没有人逼迫信托人犯罪。但信托业界也没有人不知道,银行低息可以吸引大把存款,但信托公司低息就揽不到一分钱,或许中经开这样的信托还可能有例外。是制度或者游戏规则决定了信托公司违规的必然性,它让你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当然信托公司几乎吸收不到一分钱存款,不是关门也是停业整顿;要么高息揽存、高息拆借,这样信托公司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现金进帐,当然也违规了。
在对前面这道选择题做出判断选择的时候,一茬又一茬信托人士们还肩负着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那就是要本着为人民、为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必须要保持社会稳定,避免造成金融动荡。在这样的神圣使命下,对于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你还能犹豫吗?我想,若是有信托人士能敢于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选择前者,那他绝对会被同行们认为不是脑袋有毛病,就是一个地道的“二百五”。20年中国信托的历史,就像一列挂着20节车皮的满载不良资产和违规业务的列车,肩负着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使命,夹着风雨滚滚向前。虽然信托人士中不乏有志之士,但谁也无力让它停下来清理完不良资产和违规业务再重新启动。也有大量的信托人士提出,信托公司的问题只有在发展中解决,在解决中发展。但无奈积痼成疾,使这些有志之士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信托公司早期的高息揽钱是主要是出于其扩张融资规模的本性。理论推理和许多实际证据都表明,从各部委、各大银行到地方政府,当初积极创办信托公司的共同动机是突破传统的高度集权、集中的计划金融体制,利用新生的信托业突破和绕开信贷计划管理的控制,在计划渠道之外建立自主控制的资金融通渠道。信托公司当时是被当成可以自己支配的对外融资的窗口,和绕计划控制的独立信贷资金来源渠道而创办的。只要能融入资金,信托公司是否不务正业,是否办成了非驴非马的东西,显然没有人会在意。相反,信托的财产管理功能或者真正的信托业务,对信托公司创办者而言,纯属“马尾巴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托公司倒是确实天生带有坏小孩的基因。
应当说,正是信托公司体制尤其是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脐带联系,是导致信托公司经营目标异化为融资规模最大化的内在原因。信托公司与银行同时面对基本相同的业务领域和客户群体,竞争无可避免。由于天生的缺陷,信托公司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不是银行的对手,于是高利率或高息揽钱就成为信托公司维系和扩张融资规模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而当信托公司因经营失败无法依靠自身的资金循环维系正常运转之时,高息揽钱也就成为借新还旧维持资金链条的唯一手段。由于资金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高昂,为维系原有规模的资金盘子,信托公司必须确保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当信托公司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干涸,进入走头无路、垂死挣扎阶段时,高息揽钱又成为其苟延生命的唯一手段。此时的高息揽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信托公司几乎可以说是见钱眼开:不论利息率多高,不论来源如何,也不论手段怎样,信托公司一律收入囊中。许多信托公司就在此时发明了堪称创新高峰的各种融资工具,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个人存款和证券交易保证金挪用情况的。这正象一个慢慢吸毒成隐的人,这时候为了毒品,已经无所顾及了。
如果说一个行业几乎所有业者都在违规犯罪,规则、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是否应该质疑?信托业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历经劫难乃至最终几乎全军覆灭,荒谬的制度安排实在难辞其咎。在这个一度金融产业极度发达、以信托公司和金融机构数量众多称雄的特区,在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岁月中,不断传出信托公司老总、银行行长或高级干部携款潜逃、神秘失踪、、判刑等丑闻。让人感慨的是,多数当年在特区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知名金融家们的命运结局多以悲剧告终,大多数都是涉案腐败或诈骗,而这种特殊勾连在我们所见过的金融案件中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但是,在被绳之以法的信托公司高管中,也有一些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公司债券罪”、“挪用客户保证金罪”等罪名定罪的。就这一类罪行而言,它与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腐败没有联系。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加显出制度安排之荒谬,因为同样的案子完全可以被判定为道德谴责意义上的“违规经营”而不了了之。而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乎任何人坐上信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位子,实际上就是身不由己走上违规经营之路的开始。有人甚至说,几乎所有违规经营的行为都可以被套上相应的刑法罪责,如果一定要追究刑法上的责任,几乎所有信托公司的董事长、。让人感慨的是,许多当事人都是在退位之后琅当入狱的,这实际上表明,历史旧帐的清算并不因时间的推移而结束。
面对信托公司的一再违规,指责信托公司不但是一种特别省事的事情,因为这就无需动脑筋去思考表象背后的东西,而且也是一种最不需要承担责任和风险的事情。这大概是信托公司在过去的多年中成为众矢之的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制度制定的责任或者裁判的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几乎是没有人提及的话题,原因不言自明。不论什么人,你只要在权力部门的权力位置,你就是真理的代表,说的话就是永远正确的金口玉言,就是法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几次亲历的事件为证:刚到信托的时候,总忘记自己已经不在政府部门。有一次一位领导来视察,说我们给他提供的报表中没有净资产,我回答他所有者权益就是净资产,领导勃然大怒,说他是研究生,也是高级会计师,“你懂还是我懂?”,领导气极败坏地说。我的上司事后要求我今后一定要记住“领导永远是正确的”。大约1995年4月,公司来了一群检查国债回购的领导,领导们先是指责我们隐瞒国债回购,我才知道我们每月上报的财务报表这些领导都无暇察看。但随后领导们提出的问题更让我大吃一惊,。最后他们拿着我们提供的文件作出了要我们缴纳罚款数十亿元的决定,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缴了几万元了事。任何在信托呆过的人都知道,这些不是故事,也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我甚至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既不签合同也不开存单,要发福利奖金时直接到该信托公司提现。这笔资金的存款利率是该信托公司最高的,由行长亲自决定后直接通知信托公司的总经理。,行长闻讯急忙赶到信托公司,先把手下一顿臭骂,接着又把信托公司的头一顿臭骂,要他们今后把帐做好一点,今后再要露出马脚就要严肃处理,严惩不怠。说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愤青,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无从考证。
既然有制度空白,有荒唐的制度和荒唐的裁判,负主要责任的就不应当仅仅单是当事人。过去的情况是,现在的情况还是,每次站在被告席上的却永远是信托公司。(未完待续。注:本文中的图片由搭配。)
最新资讯
-
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营销服务革新:建立高效的销售体系,加强销售队伍建设
01-10 2
-
08-13 0
-
08-25 2
-
08-27 1
-
08-28 0
-
08-25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