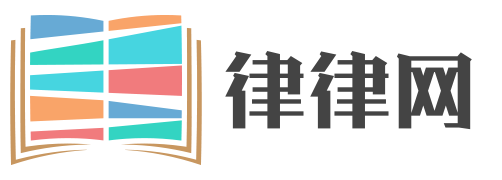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
发布时间:2019-08-31 12:55:15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在于资金。根据权益与义务配比的原则,社会保障资金应该由政府——企业——居民个人分项负担。从居民个人来看,预防性储蓄假说已经表明了个人在积极地进行自我保障,这为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难题。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即它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根本上制约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大部分责任。
政府如何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和变卖公有资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政策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一)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实质上是解决资金拖欠,使之能及时、足额取得的问题。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初步设想是将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等五大收费项目“费改税”。然而这一设想无助于改变目前资金筹集的困难处境。因为:(1)中国社会保障的范围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机关的职工,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收费理所当然地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会保障费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征新税后,名称的改变不会对税源的扩大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2)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林达尔均衡在现实中极难实现,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税收征管严密著称的西方诸国中尚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法制极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平常不过。(3)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后,“欠费”现象是消失了,但不过是以“欠税”代替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还略胜一筹。政策性收费已经具有了税收的强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税都是国家强制力的表现,名称的互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统一的税率可以解决政出多门、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若要达到此目的,从行政上进行改革做到政令统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益的提高,并且应有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执法来保证——社会保障税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效力。
(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一般是以工资收入为课税对象,普遍实行累进税率。“职工个人以工薪收入、国有企业以职工工资总额、个体与私营企业主以缴纳所得税为纳税对象,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应纳税由政府预算直接安排”的税制设计,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预开征的社会保障税的课税对象与已开征的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源。对个人(含个体工商户)的课税客体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对企业的课税只不过是企业所得税的翻版。因为企业的计税额是纳入成本的,最终只不过是在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同时,增加了社会保障税而已;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手从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缴纳社会保障税或直接由政府安排,这对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意义不大。另外,如果说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动因是要解决收费中的高成本问题的话,那么过高的税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税的实施效果不容乐观。课税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其所得税提高1%导致每筹集1美元的税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达到增加收入额的17%—56%。而中国,税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维持这样的税收收入——成本比率,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成本只会水涨船高,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抛开社会保障税开征障碍的其它原因不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目前,政府以无偿的即期收入(税收)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它在未来税收秩序理顺后自然应该是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2)居民应债能力偏低。整个20世纪如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下面对以上理由进行剖析。
1.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的财政债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债务或国有部门债务远大于现在所计算的财政债务。其中造成差别最大的两个项目,一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一是隐性养老金债务。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至少达12000亿,这是资产管理公司将要接收的总额。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部分只能作粗略的估计。一是没有回收希望的坏帐,即按新的贷款分类法划分的第五类贷款。按目前的政策,这些贷款不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由银行自己冲销,这种不良贷款至少有3200亿(张春霖2000);二是1996年1月1日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它不包括在12000亿元之内,按估计应在8800亿元左右;三是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三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当在3000亿左右(朱民1999)。如此算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1999年GDP的24%。相比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取决于未来几十年的一系列经济参数变化,包括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工资率等。按照世界银行1996年的测算,这部分债务相当于1994年GDP的比例在6%—40%之间。仅仅把银行不良资产损失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加在一起,占1999年GDP的比例最高可达64%。如此,无法得出中国宏观债务率在安全线以下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债悖论(刘溶沧1999)不存在。做出这样结论的一个根本依据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多年改革并没有根本上改变这一性质。财政、银行、企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的三个钱袋,相互间的独立性十分有限。中国仍然面临末完成的改革。
最新资讯
-
08-28 0
-
08-13 2
-
08-11 1
-
11-05 1
-
05-22 1
-
04-2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