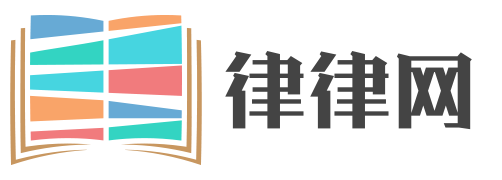酒后驾驶主观罪过的司法认定
发布时间:2019-08-24 03:24:15
酒后驾驶主观罪过的司法认定
(一)原因自由行为的罪过问题
在危险驾驶犯罪中,主观罪过难以认定的往往是那些原因自由行为,比如部分酒后驾驶犯罪。无论是在本国刑法中明确规定原因自由行为之责任的国家,如瑞士、意大利、波兰等国,还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都是在理论上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我国刑法也没有对此进行专门规定,但刑法典第18条第4款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之规定,涉及到原因自由行为问题。因此,在办理酒驾、醉驾等犯罪案件时,若不加区分地对每一个案件都去追查行为人在造成严重后果之时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纠缠于此,显然是缺乏原因自由行为之法理意识的结果,这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有害司法公正。
中外学者对原因自由行为表述不一,但一般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包括4种情况:(1)故意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刑法规定的客观要件行为;(2)过失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刑法规定的客观要件行为;(3)故意使自己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刑法规定的客观要件行为;(4)过失使自己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刑法规定的客观要件行为。[7]前两种情况较为少见。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可以把整个行为过程区分为原因设定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惹起行为(或结果行为)两个阶段,而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要回答的就是,在结果惹起行为实施当时,行为人处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却为什么能够正当地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现代刑法遵奉“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或不降低其刑事责任(因为各国刑法一般规定对限制责任能力者的犯罪减轻其刑)。针对此问题,日本学者有“间接正犯类似说”、“原因行为时支配可能说”、“意思决定行为时责任说”、“相当原因行为时责任说”等观点之争。[8]笔者认为,以往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于上述(1)、(2)两种情况的研究较为成熟,据此处理个案通常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对(3)、(4)两种情况的研究却欠火候,甚至有的学者想当然把对前两者的研究结论推及到后两者的解释上,结果却解释不通,而有的学者则干脆否定后两者属于原因自由行为,结果是回避了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目前处理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犯罪案件时遇到的不好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司法难题,正与这种研究状况有关。因为,在(1)、(2)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只要查明行为人于原因设定行为时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结果惹起行为时处在无责任能力状态,并且原因设定行为与结果惹起行为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足以认定犯罪故意或者过失,不存在判断结果惹起行为时的罪过问题;但在(3)、(4)两种情况下则不然,由于结果惹起行为时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只是有所降低,那么就需要判断犯罪故意或者过失究竟是“原因设定行为”时就有,还是到“结果惹起行为”时才有,也需要判断故意或者过失在从前行为向后行为的发展过程中有无质变。
在(3)、(4)两种情况下,由于原因设定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而后在结果惹起行为时行为人只是辨认或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因此要把原因设定行为与结果惹起行为联结为一个整体行为,就不仅需要前后两个行为阶段之间具有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还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的罪过心理连续性。因为,在(1)、(2)两种情况下,结果惹起行为是在无辨认控制能力下实施的,不可能要求罪过心理的连续性,只要是行为人在原因设定行为当时有意利用社会平均人认为“自然而然”的客观过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前后阶段评价为一个整体行为而追究刑事责任,这符合社会平均人的法感情。(3)、(4)两种情况则不同,如果不考察结果惹起行为时行为人的罪过性质,而只考察原因设定行为时的罪过性质,或者相反,只考察前者而不考察后者,都可能由于行为人罪过心理的不连续性而轻纵或冤枉罪犯。具体说,在原因设定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某种犯罪的故意,但在结果惹起行为时行为人的罪过心理已转变为另一种犯罪的过失,此时如果只考察其前阶段的罪过心理而不考察其后阶段的罪过心理,则会以某种故意犯罪定罪处刑,往往会冤枉行为人;而此时如果只考察后阶段的罪过心理而不考察前阶段,则会以某种过失犯罪定罪处刑,并无视原因自由行为的存在,往往会轻纵行为人。因为,本应认定为某种故意犯罪(预备、未遂或中止)与某种过失犯罪并罚的行为,却被认定为某种故意犯罪(加重犯)或某种过失犯罪。在原因设定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某种犯罪的过失,但在结果惹起行为时罪过心理已转变为另一种犯罪的故意,此时如果只考察其前阶段的罪过心理而不考察其后阶段,会轻纵行为人;而此时如果只考察后阶段的罪过心理而不考察前阶段,也会轻纵行为人。因为,本应认定为某种故意犯罪的行为,却被认定为过失犯罪,或者虽认定为故意犯罪,却否定了其原因自由行为,从而因行为人责任能力有所减弱而对其从宽处罚。笔者认为,此时原因自由行为虽非完整形态,但毕竟残存着,对此时行为人的故意犯罪不应因限制责任能力而从宽处罚。在原因设定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某种较轻犯罪的故意,但在结果惹起行为时罪过心理已转变为另一种较重犯罪的故意,此时如果只考察其前阶段的罪过心理而不考察后阶段,会将较重之罪误判为较轻之罪;而此时如果只考察后阶段而不考察前阶段,可能在认定较重之罪的基础上不合理地给予从宽处罚。在原因设定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某种犯罪的过失,但在结果惹起行为时罪过心理已转变为另一种犯罪的过失,此时如果只考察前阶段的罪过心理而不考察后阶段,或相反,只考察后阶段而不考察前阶段,都会导致定罪量刑的失误,恕不详述。
因此,在判断酒后驾车等危险驾驶犯罪主观罪过的问题上,难中之难在于审查判断这种罪过心理的连续性。接下来试作讨论。
(二)前后罪过心理的具体判断
危险驾驶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同为交通参与者,常常处于对自身亦有危险之行为环境中。加之交通环境是流动而富于变化的,所以危险驾驶犯罪的隔地性、隔时性明显。据此,在判断行为人的罪过心理时必须考虑到以下部分因素:
其一,行为人的人格状况。20世纪中叶以后在刑法学中兴起的人格行为论,把刑法所规制的行为,理解为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人格行为沦为基础的人格不法理论,将对犯罪的刑法评价建立在具体的、个别的行为人的人格评价基础之上,从而为刑法评价超越形式正义而趋向实质正义开辟了道路。我国学者指出,人格反映人与人的本质区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用人格不法的概念来评价犯罪的行为和行为人,比传统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等概念更为科学。[9]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不能把行为人看作抽象的社会平均人。如果不考察行为人的人格,一方面很难认定行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另一方面也往往难以判断罪过心理的连续性。有的危险驾驶行为人,具有正常人格,甚至是生存状态良好,心态乐观向上,没有任何自杀或厌世心理,更没有报复社会的动机,说他(她)在实施原因设定行为或结果惹起行为时具有放任严重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往往不合情理,而说他(她)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放任的故意具有连续性,更不合情理。而有的行为人,,不仅贱视自己生命,也漠视他人生命,甚至有暴力犯罪的前科,说他在实施原因设定行为或结果惹起行为时具有放任的故意,乃至希望的故意,常常人情人理。尤其是对于前述(1)中之行为,如果说在明显非对等(这里指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生命安全所受威胁不对等)的行为环境里,人格正常的行为人也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放任他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在交通危险基本对等的交通环境里,人格正常的行为人实施该种危险驾驶犯罪则是难以想像的。当然,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人格调查需要一套科学的、民主的司法听证机制,目前在我国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但即使是在目前,司法机关也应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现实作为处理危险驾驶个案时判断其罪过心理的重要背景信息加以考虑,这并不表示要以人格调查取代行为评价。从根本上说,在定罪过程中是否有行为人人格因素的容身之地,关乎前文所提到的司法官的法律观和司法观问题,限于论题,在此不作进一步探讨。
最新资讯
-
11-28 1
-
08-13 1
-
08-22 2
-
08-11 0
-
08-14 0
-
08-0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