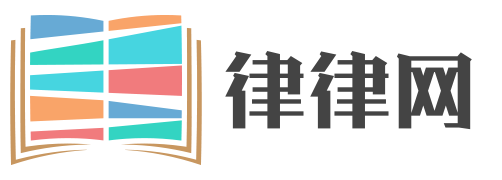论人格权的本质
发布时间:2020-05-11 06:23:15
[提要] 民法(草案)》*1 将“人格权”在分则中单列一编(第四编)做出了规定。支持者认为这一做法为极富中国特色的创新,*2 反对者则认为其混淆了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3 争议不可谓不大。但现有争议多集中于法典内容体系安排之逻辑性方面。笔者认为,人格权应否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立法体系安排问题,但其实质上首先涉及人格权的性质认定,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既有观念和理论存在诸多谬误。为求我国未来民法典之科学性,本文特对此发表意见,以资参考。
一、“人格”:私法上的概念抑或公法上的概念?
人格权与人格的联系如何?此为有关人格权问题论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观点强调二者的联系,指出“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义”,*4 故无须单独规定;相反的观点则试图疏远这一联系,指出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人格权所谓之人格非属同一范畴,*5 并由此而将人格权视为一种与物权、债权以及亲属权得相提并论的民事权利,成立其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基本理由。
事实上,尽管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遥远,*6 但人格权与人格之更为紧密的联系却不容置疑。为此,论证人格权的本质,须从论证人格的本质开始。
依通说,“人格”理论肇始于罗马法。过去的理论,多将罗马法上的“人格”依现代观念理解为纯指自然人的民事主体资格(即私法上的主体资格),但新近有学者指出,罗马法上的“人格”,首先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在罗马法有关人的三个用语中,“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caput”指权利义务主体:“persona”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7 一个人必须同时具备自由人、家父和市民三种身份,才能拥有caput,即在市民名册中拥有一章的资格,才是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否则,就是奴隶,或是从属者,或者外邦人。*8 由此,caput被解释为罗马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所谓罗马法上的“人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由人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和家父的身份所构成的城邦正式成员的身份问题,亦即人格的拥有问题(公法领域),然后解决“作为一个私的团体”(即家庭)首脑的家父身份即家父权的展开,亦即家庭内部关系问题(私法领域)。而由于此种“人格”实质上是关于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划分,是作为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一种工具,所以,在罗马法上,“人格”具有公法性质。*9 当然,考虑到“人格”在罗马市民内部(私法领域)确定交易主体资格所具有的意义,将之认定为“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10 也是基本正确的。
罗马法上与人格有关的persona一词,后来成为现代法理论上“人格”(personality,personalité)的辞源。*11
作为近代民法开先河者的《法国民法典》上没有关于“人格”(personalité)的直接表达。但该法典第8条之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后来被认为是确定了自然人之平等抽象的人格。但已有学者指出,法国民法的此条规定虽然确定了法国人之平等的民法地位,但其另外的目的,却在于排除非法国人(外国人及无国籍人)对于私权的当然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奴隶制度存在于法国殖民地,直至1848年方始废止)。而在法国的论著中,“人格”(personalité)之有无,被用来描述自然人是否适用法国民法,甚至用来直接代替民法典上对此采用的有无法国国籍之区分的标准。*12 由此可见,至少在《法国民法典》颁布时期,如果说该法典对于“平等人格”作了某种宣称的话,其仍然具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认定作用,此种“人格”,仍然直接具有宪法上的意义。
常令人迷惑的是,在《德国民法典》上,不仅没有关于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宣称,而且该法典采用极端技术化的“权利能力”(Rechtsf?higkeit)概念取代了“人格”。而此后的瑞士、日本以及旧中国民法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等纷纷跟进,“人格”的概念不仅在立法上隐而不见,且在理论学说中几近被“权利能力”所替代。由此引起的论争是:“权利能力”是“人格”的替代品吗?对之,尽管众多的回答都持肯定或者基本肯定的态度,*13 但答者均无法回避内心深处的犹豫,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回答接踵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用含义并不清晰的“权利能力”去替代“人格”?
现有资料表明,权利能力之概念,为学者Franzvon Zeiller(1753-1828)所起草的《奥地利民法典》中第一次在立法上使用。*14 对于权利能力的本质,德国学者间便有完全不同的看法:Gierke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权(一种权利),H?lder认为权利能力为享有权利之资格,*15 而Fabriciushe 和Gitter则认为权利能力由行为能力所派生,为从事法律上有效行为的能力,Larenz和Medicus则主张坚持对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即权利能力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16 很显然,在德国民法理论上,无论对权利能力作何理解,权利能力都没有被直接解释为“人格”的同义语,此为一重要事实。
至于德国民法为什么创制权利能力制度,以及为什么这一制度被后来各国的立法所承继,如果不从德国民法独特的形式理性思维方式去理解,那将是很难理喻的:众所周知,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制订的民法典以及受潘德克吞(Pandectae )法学影响而建立的民法理论及立法体系,都是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基础而编排的:民法典之总则为法律关系的共同要素(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以及权利义务的共同准则),分则则是对四类法律关系的具体规定(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在这种系统编排法中,由于法律关系的概念在表现法律体系所适用的社会现实上被认为是合适的框架,因而其被用作整理法律及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范对象,而民法之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便在于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hominum causa omne ius constitutum est)。*17 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资格,即权利能力或者主体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担负着完成法律关系形式结构的任务,并不当然具有表彰或者替代“人格”的功能。为此,《德国民法典》在采用权利能力的概念时,并未对之加诸定义。而其后《瑞士民法典》对权利能力作了进一步解释,规定“自然人享有权利能力”(第11条第1款),“在法律之范围内,人人均有同等之能力,有其权利与义务”(第2款),强调主体资格之平等性。据此,权利能力所隐含的“人格”价值便得以彰显,以至于为理论上进一步扩张权利能力的功能使之与“人格”几近等同提供了依据。但是,尽管权利能力毫无疑问是人格的表现,但较之权利能力,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其描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限于私法)、一般意义的权利主体资格(不限于私权),在此,即使将权利能力阐释为“享有总和之权利的资格”,与直接表达和体现人之尊严、平等及自由的“人格”,仍有角度、范围和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最新资讯
-
08-28 0
-
08-05 2
-
08-31 2
-
01-01 0
-
08-19 1
-
08-29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