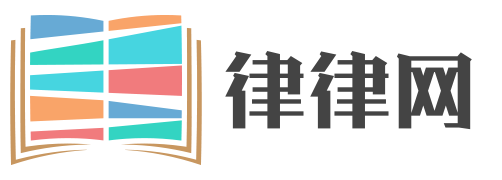郑成思:我的知识产权研究之路
发布时间:2019-08-05 12:31:15
我怎么研究起知识产权来了
1979年4月,""之后我刚刚"归队",经历了农场、矿山、教员、政工干部等工作岗位后,回到了法学研究岗位,进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被安排到国际法室。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中国去该组织开会的代表团,带回来一本《有关国家商标法概要》,当时它是该组织的最新出版物之一。我国正考虑要制定《商标法》,为借鉴外国的已有条文,当时的商业部、贸促会、政法学院、外贸学院等单位,想组织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
这本大16开240页的书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首先就给人以"工作量太大"的感觉。"商标"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商品包装上贴的纸签吗?《商标法》与国际法、民法、刑法等等比起来,显得太窄,地位太低。这又使人感到"犯不上为它花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几个月找不到人愿意翻译它,是不奇怪的。那时"知识产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很陌生,远不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及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把它炒得这样的"火"。
后来一位领导要求我来试译一下,是否愿意最终接下全部任务,可以试过之后再说。我历来属于"好说话"的一类人,很少轻易地顶撞领导。但我知道这是一部许多人不愿接的书,我自己的英文水平及精力如何,自己并没有把握。而对于可能卷入这样"窄"的学科中去,当时心里是不愿意的。只是抱着"服从领导"和"试试看"的心情,硬着头皮接下来了。
在译前几个目录的法条时,真有点急得"灵魂出壳"了。当时正值三伏天,面对一大堆自己根本不熟悉的术语---在已有的国际法、民法及刑法的中文里,完全找不到它们的对应语。"把它扔下干别的",曾是第一个掠过我脑海里的念头。确实太难了,有时一句话困扰了我一夜,也未想出合适的译法。
我请教几乎与我同龄的商标专家王正发及作为学长的国际法专家姚壮时,他们都讲了几乎同样的话:"有些术语,中文里原本没有,你可以大胆译---当然要慎重、要确切,译出之后,就'从无到有'了,今后人们就可能随你的用法。""找不到中文的对应术语,说明你的工作是开拓性的。"同龄人及学长们的话,无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几度浮起的半途而废的念头最终被打消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请教过几十位国际法、刑法、民法领域的专家,请王正发先生全文校改过其中一个国家的商标法的整篇译文。这半年里,我几乎是全神贯注地投入了这本书的翻译。在30多岁的年龄,原有的近视度数又增加了50度。
不过那本书终于译完了。近百万字的译文,得到了60元还是80元"翻译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在那之后,我再动手翻译《专利法基础》一书时,已经不感到十分费力。
1981年,在顺利通过了所、院及国家三级英文考试后,我前往英国留学,成为1949年后我国派往英国的第一名法学领域留学生。也就是说,在专业上,在外文上,经过那半年的翻译,自己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对知识产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了解了知识产权法与传统民法的联系与区别,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知识产权中"依刑法而产生的民事权利",知识产权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将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当初的半年翻译活动中闪现在脑海中的。当然,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则是其后20多年中的事了。
在后来这20多年中,我先后写出了中、英文专著30余部,,有的成为全国高校统编教材。这些专著中的不少术语,已被今天国家的立法及许多人的著述广泛使用。而它们均源于那本红皮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标法概要的第一个中译本。有的译法可能是我自己确定的,有的可能是与王正发、姚壮等专家商议后共同确定的,还有些则可能是这几位专家确定,我认为正确而采用的。
1982年在英国学习时,有一次,我不知怎么有了这样的念头:如果不译这本书,我不可能把英文提高到能通过三级考试的水平,也不可能选择知识产权这个专业方向,因此应该在手头留有这样一本书做纪念,也好打消自己经常冒出的"偷懒"念头。我虽然自信是勤奋的,但未必不想偷懒,尤其在感到劳累时。当初如果回绝了领导派下的任务,如果干到一半就放弃了,也不会招来什么很坏的后果,自己倒可以轻松轻松,不过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留学机会了。
于是我写信给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部,要求买一本《有关国家商标法概要》,因为在1980年初翻译完成后,该书的原本已交还中国贸促会。出版部的负责人显然没有我们今天许多人那种"经济头脑",他复信说书中的有些法条已经变更,所以当该组织准备出新版时,我准备买一本,该书要400瑞士法郎,有人劝我不必花这笔冤枉钱。不过我仍旧邮购了一本,结果连邮费花了我当时两个月的生活费。从伦敦的邮局收到该书时,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终于有了一本属于我自己的、我曾为译它而花费了那么大精力的《商标法概要》了。
回国后,这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架上。有时我也用到它,特别是遇到知识产权法条或国际公约条文的翻译障碍时,就会想起该书曾出现过相同或类似的句子、条文或术语。但这样的使用机会毕竟很少。更多地使用,是让它作为一个时时推着自己往前走的动力,使我经常想起当初因何选择了知识产权这个研究方向,回忆起当初困难的条件。既然当初都挺过来了,现在更不应当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
当众给导师"指错"
引发了对我的"惩罚"
在英国学习,我选择了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国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均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该校学习。进入80年代,该校柯尼什教授又出版了当时在发达国家最有影响的知识产权教科书《专利、商标、版权与有关权》。这便是我选择该校的两个主要原因。
从学长们过去的介绍中,我只知该校校风较好,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甚至是严厉。知识产权课的主讲人正好是柯尼什教授(同时也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也是这种严格与严厉风格的化身。
最新资讯
-
08-16 0
-
09-01 0
-
08-19 0
-
08-27 0
-
08-15 0
-
08-23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