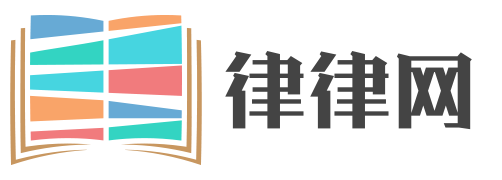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刍议
发布时间:2019-08-19 20:07:15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多种形式,主要包括转让、入股、抵押、租赁、继承、转包,以及一些特殊问题,如征收、建设占用、集体撤销承包、抛荒、调整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一种,但无疑是最为重要和最具争议的一种流转方式。不管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对转包、出租和互换等暂时性土地流转方式大都认为应当鼓励,但对转让、入股、抵押、继承和赠与等永久性土地流转方式则有很大分歧,多持保留态度。其中,入股只是发生权利的置换问题,设定抵押也只是产生权利的限制问题,仅使权利具有移转的潜在可能性。其实, 解决了“转让”的问题,入股、抵押、继承和赠与的厘清就可水到渠成。当重新审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时,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权利? 是否应当允许其转让? 对转让应作何限制? 转让的程序是什么? 应有哪些配套措施辅佐?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先天不足的用益物权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农民自发探索与国家政策承认并调整的双向互动基础上形成的,逐步经历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2]土地承包经营权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凤阳小岗村18 户农民的“大包干”,但1982年《宪法》并没有认可这种承包经营。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全国农村开始普遍推行包干到户,实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保证了农户的独立经营权; 1986年的《民法通则》和《土地法》对承包经营权做了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开始进入立法; 1993年《宪法》也正式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先后出台,在立法上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定位。
由上可见,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前,农地的土地利用问题纯粹是政策问题、经济问题,在国家对农民反复的收权放权之间,,着力于恰当配置利益关系以实现农民生活温饱和农村经济繁荣。在这里,私法的调整存在着缺位的状态,农民也从未享有过对土地的民事权利。这之后,随着各项法律的相继出台,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私权出现,并不断地在与公权力的博弈过程中取得更多本属于它的领域范围。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物权法》中的专章规定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但在舶来的民法概念体系下,现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像是一个杂糅而成的“混血儿”,无法轻易地对其做出清晰界定。
现行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摆脱了长期以来依靠红头文件保障土地承包经营人合法权益的尴尬局面,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4]但是,脱胎于权力深度介入的土地利用制度、生长在权利意识淡漠的土壤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其质态具有多样性、不稳定性和临界性。它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用益物权,甚至可以说徒具物权之名,而无物权之实。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承包人仅具有残缺的处分权能,支配力受到极大限制。《物权法》第128 条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要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流转,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 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具备几项条件,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发包方同意,受让方为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从理论上看,我们无法观察到在私法意义上传统的物权取得方式,在操作层面,集体土地的范围的确定最终乃是行政划界的结果,其合法性来自于行政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在的合理性:不是你买的,你当然也不能卖,补偿给多少算多少,因为给你补偿的,刚好就是为你划界的那位。这里面的逻辑并没有错。[5]转让须经发包人同意的说法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存在显见的抵牾。除此之外还有哪个他物权本身的处分还要求诸于所有权人的同意?对出让方的非必要限制和对受让人的歧视性区分也绝非一项物权的题中之义。在这种集体经济之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没有被定位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财产权利,这种集体土地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人身性和行政色彩。
最新资讯
-
08-29 2
-
08-27 0
-
08-14 1
-
11-24 1
-
08-17 2
-
08-2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