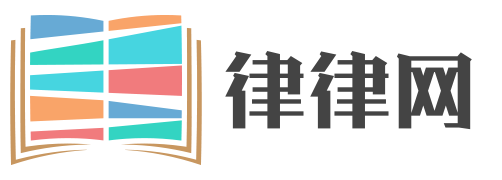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法与其替代制度
发布时间:2019-08-26 05:23:15
现代社会道路交通事故频发,各项应对制度之设计早已超出早期侵权法制度的范畴。本文在篇幅上为一学期论文,仅能就侵权制度与侵权法之替代制度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体现的理论背景作简短勾勒,就法律制度特点利弊作简明铺陈。因交通事故与医疗制度、劳工事故等其他意外事故中均含有侵权法与其替代方案之间的对立因素,交通事故与其他意外事故补偿方案间存有制度间覆盖上的划分与衔接,这些本身是复杂的问题;但这些制度有共通之处,即在于弱化侵权所含的招牌式的过错要素,而改之以社会福利的面目出现,本文将有意图的模糊这些侵权法制度的替代制度之间的区别,而赋之以对应于侵权法制度的观念上的整体。
一
侵权法的思路是承担责任要行为人具有过错,除非特例责任不应当是严格的。第三方保险与第一方保险的区别大致就是侵权法与替代制度的区别。第一方保险的基本含义是,不考虑过错,不考虑事故的起因,事故的受害人从自己的保险人处去的赔付。而第三方保险从来就是与侵权法一同发生作用的。
传统上普通的侵权制度,以普通法为例,大致特点是:普通法上过失之诉的主要特征:[1]原告如能证明所受伤害由被告的过失引起将获得回复;“全部的”赔偿指,使得受害人恢复到如同损害没有发生过的处境中。如果受害人自己的过失促成了事故的发生(构成“与有过失”)损害赔偿按他的责任份额成比例减少;原告的损害赔偿以永久性的一次性方式估算,包括所有过去和将来的损失。这里列举的特征同时构成了反对普通法接管的理由,因为在司法程序中证明侵权责任总是很困难的,原告方要完成证明足以补偿受害人遭受损害的赔偿范围更难,第三者责任险曾经是意图帮助侵权法应对困难的工具,但是仍不够得力;其原因是:在制度运作机理上第三者责任险实际上躲在侵权行为法身后,只有当被保险人对他人受到的损失承担责任时才会被触发;与此相反,第一方保险是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的制度与侵权成立与否并不相关。而第三者责任险兼具双重保护目的:就被保险方侵权行为人这一制度提供免于出现不利判决时承担灾难性结果;就受害方而言保险提供了获得赔偿的保障。[2]
最初的制度设计思路是依靠责任保险提高法律制度整体对受害方的保障能力。
根据一九三二年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研究报告,一半以上的载客车辆的所有人没有责任保险,赔偿请求权往往不能在他们实现。有三个州的立法要求机动车强制保险,余下四十七州立法上规定,如果驾驶者造成事故后不能负起金钱上的责任,这将危及他的驾驶特权。由于这些责任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许多州中90%的道路驾驶者都拥有责任保险。
效果:大范围的责任保险使得小额赔偿获得慷慨解决的数目大为上升;造成死亡和重伤的伤害也更容易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但对重大损失的弥补通常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少得可怜。
机动车责任保险所占的保费达到了保险公司收缴保费的一半强;而权利人获得的赔偿加在一起不到所有驾驶人缴付的责任保险费总额的45%。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立法首次要求无过失保险。大多数已通过的计划所提供的制度都是由相对较少的无过失保险金加上保留侵权制度应对除了小额索赔之外的所有赔偿。
在道路交通事故领域,即使在行为人已经达到相当的注意程度时,机动车事故仍然会不断地发生。机动车本身的高度危险性是事故的根源。如果无法避免人身伤害,而且伤害是因为行为人具有普通法上的过失或是行为人违反制定法规定的注意义务,社会的期望是由加害人来承担责任,事实上加害人也会通过保险来对抗被施加侵权责任的风险。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赔付范围包括:身心痛苦、失去愉悦之精神损害、失去工作能力、失去营生能力带来的损失、为提供看护而支出的费用。这些赔偿的来源只有三处:来自受害人、来自国家、或是来自不法行为人。个人是赔付能力最弱的来源,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唯一的来源。事故中的责任原则之争是适用严格责任或是过失责任之辩。前者主张无论加害人施加的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风险负担,都要承担事故发生的责任;后者主张侵害人仅对施加不合理的风险负担所引起的事故损害承担责任。本文认为危险性活动(伴随事故高发)适用后者。侵权法不得不艰难地改变自身的规则以适应后果严重到灾害式的交通事故,这一难以避免的社会顽疾,侵权法的目标也正缓缓地有阻遏倾斜到赔偿,这些内部的改变帮助侵权法体制并不会轻易地遭到废止。而侵权法的这些内部努力正是借助责任保险而完成的。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的早期,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实际承担完全是由侵权人自己担负。随后出现向车辆所有人提供的任意性商业第三人责任险,这些商业保险一般仅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和各项费用的支出所带来的财产损失,在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建立起来之前并实际为赔付之前,保险公司并没有为被保险人向受害之第三人为给付的义务,可见此种责任保险规定旨在填补损失重于保护第三人免于伤害之苦。最初始形态的自愿责任保险制度的重心落在填补被保险人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上,几乎并不考虑受害人能否得到赔偿的问题。之后由于法律特设了第三人(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使得受害人从判决中获得赔付的机会增大,责任保险制度对损害分担、扩散损失的作用始得显现,进而机动车责任保险开始对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法规则开始真正产生影响。
责任保险的存在使得法官和陪审团在给与补偿时更为慷慨、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保险人在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权利介入,有权为被保险人辩护的权利(同时也是一项义务)以及拥有进行和解的权利,保险人出于降低日常运营费用的考虑往往愿意和解而非诉讼,保险人会倾向于免去部分本来用于确定过失的例行公事式的调查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受害人地位,使受害人获得及时赔偿变得容易一些。
强制机动车保险的出现对侵权法司法裁判方式产生影响。保险的无处不在对侵权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法律归责原则发生改变。
,,丹宁指出:理论上,。但他们仅仅是假装如此,、保险公司和纳税人;“那也就是为什么过失法可以扩展到几乎人们从事的一切活动,那也就是为什么损害赔偿判决数额高到了即使是最富裕的个人都无法赔付的原因”;[3]长久以来英美法国家法官一直不愿提及的事情就是:广泛存在的人身伤害保险与侵权法律发展之间的关系。根据传统理论,法官在做出判决时不应当考虑保险确已存在或是可能会存在,保险应当被有意识地忽略,应当被法庭视作不相干的因素。但这种情况已开始转变。,之后法官更是在实际的司法裁判意见[4]中承认,。尤其是在人身伤害案件场合的处理中确确实实可以感受到保险存在的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强制保险普遍存在,、设立可推翻的假设、采用事实自证等方式弱化过失责任的使用效果。这些司法实践有利于受害一方获得赔偿。而通过为过失侵权法判决提供了更为可依赖的、更具有现实化可能的经济资源,责任保险确实加强了侵权法的赔偿功能。
过错推定、事实自证、可推翻的推定等等制度协同下的过错责任原则实际上是以类似于无过失责任原则效果的方式运作。[5]在事故赔偿领域,责任保险和无过失责任原则的结合或是责任保险制度与变通的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两种方法都可以被看作是侵权法法律改变过失归责为主导的理论而寻求新的方案的尝试。意外事故法律对整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侵权法律而言是一个例外。在这里,过失归责逐渐成为非主流意见,尤其是在涉及赔偿范畴中的人身伤害时,过失不再是对于建立赔偿而言牢不可破的概念。
扩展使用“严格责任”毕竟仍然意味着与侵权理论保持关系,仍然暗示着金钱成本仍是由那些直接参与风险制造活动的人群承担。责任保险虽然是依附于侵权责任,然而正是它的存在帮助侵权法将赔偿的目标摆到了较之以往更前的顺位,极大地促进了侵权法对赔偿问题的重视。不但如上文分析介绍那样,在道路交通事故领域中发生了侵权法内部无过失主义全面冲击过失主义的理论争议和立法例变化,而且无论是坚守改头换面的过失主义还是采用直截了当的无过失主义,侵权法都是实际借助了责任保险制度或是凭借责任保险制度才完成其本身难以承担的损害分担的功能。
笔者对此的看法是,责任保险并没有免除普通法的过失标准,过失的证明仍然是一个令受害人难以获得充分及时有效赔偿的主要原因。责任保险本身并不是一项为充分赔偿受害人而设的制度,在设立之初,这一设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障已付出赔偿的被保险人,而非要成为任何一项增进社会福利的方案的一部分,它的这种本质绝大多数地保留了下来。[6]因为属于一项填补损失的财产保险,保险人是否需要赔付,取决于受害人能否依照侵权法过失原则建立起加害人/被保险人的责任,而在早先被保险人若无财力去承担侵权责任,保险人没有义务向受害人支付,常常因为受害人无法证明加害人/被保险人的过失从而无法建立起责任而不需要发生理赔,新的呼吁新的调查往往强调:传统普通法往往对交通事故受害者救济不利。许多受害者常常根本无法律救济。举一个学术作品中列述的对此表示不满的例子,[7]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界时不时敦促立法改变交通事故法律的特质,而几乎所有提议都纳入了这两条内容:即无须证明被告过错即可产生责任以及不可使用与有过失作为抗辩。[8]主张改革者把从事实性研究中得出的数据用作反对侵权法制度的基础。这些数据表明:其一,受到轻微伤害的权利人得到的救济往往大大超过他们受到的损失。其二,受到严重伤害需要延长治疗及康复治疗或是因残障而收入大为损失的人,却极少得到仅及其损失一半的赔偿,经常是一点点补偿也没有。其三,事故中死者的幸存方与受严重伤害的受害人同样受到恶劣对待。其四,大多数大额赔偿旷日持久。时至今日,对司法诉讼的批评仍见报端。[9]坚持过失主义在交通事故领域并不妥当。传统上过失必定与道德上的可受谴责性联系起来,一般只有在出现可受谴责性的场合才有过失侵权法。众所周知,道路交通事故的产生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假设其他条件均等,驾驶人的行为才是造成事故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驾驶者的一般驾驶行为是否有过失呢?判断在多数道路交通事故中,驾驶人是否具有过失以及存在过失是否是普遍的现象,应当首先分清“过错”和“差错”(fault v. error)。考虑到驾驶一个高速非轨道运动的现代高灵敏度机械的人类都是平凡的血肉之躯,多数促成事故发生的人类动作严格说只是“差错”而非“过错”,过错的含义意味着行为本身是行为人可以选择的结果,这种出于意愿的选择的结果不符合社会因而具有可受责难性。[10]机动车事故的发生更多地是源于机动车本身的高度致损害发生的可能,危险性根源于其事理本身,而多不在于行为人的过失。[11]如果法官想要保存过失归责原则和过失错概念的纯洁性,就不应当混淆了过错和差错的区别。由于多数机动车事故发生本身欠缺道德上可非难性,事故损害更是不可避免和不可躲避,很多事故场合并不能确知损害事件因果关系两端的加害人和受害人,在事故领域适用过失主义会造成不妥当的局面。这就为采取全新的社会化、一体化不考虑过错的分担方案提供了正当性。交通事故损害的社会化分担正是由于事故责任难以从道德层面无争议地施加给个体承担,而转向推动由施加群体性风险活动的整个群体承担的方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立法首次提出无过失保险方案。罗伯特·基顿(Robert Keeton)与杰佛瑞·奥康纳(Jeffrey O’Connell)于一九七〇年提交了一份报告。一九七二年由各州组成的准官方机构“国家统一州法律委员会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通过了《统一机动车事故赔偿法》,这份报告成为美国各州对无过失保险立法的核心内容。本文依据此法案介绍无过失补偿方案的基本内容:
(一)在机动车事故中,即使造成损害的驾驶人已经尽了适当注意义务同时受害人的过失促成了对自身己伤害的发生,保险补偿方案仍然应当就由事故引起的经济损失提供一定数额的救济。
(二)受害人有权要求就所有的合理的医疗与康复支出要求赔偿;其次就由机车事故引起的收入损失以每周不超过二百美元可获得补偿,同时这一部分补偿可能因受害人从其他的来源中(劳工赔偿保险或健康保险)得到补偿金而部分扣除。
(三)允许机动车所有人以同意接受各种减少部分自己及家人的特定无过失补偿金的减额赔偿方案,选择减少保险费的支付。
(四)无过失保险赔付排除所有对故意自伤者及在使用偷盗机动车时受到伤害的盗窃人,此点将在保单中间列明。
(五)所有立法上的改变均不影响本方案所规定的躲避参加无过失保险法定义务的驾驶人在普通法上的责任,也不影响故意伤害他人的驾驶人的责任。
(六)对受害人自最初受到伤害之日起超过六个月之后仍发生的收入损失部分,驾驶人将承担所有的普通法上的侵权责任(包含普通法上的所有通常的限制)。
(七)机动车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因在赔偿事宜拖延期间死亡。如果相关制定法为因过错行为致人死亡事件中的死者的生存人回复发生于事故与死亡之间的收入损失,生存人回复的无过失补偿金中收入损失的部分不得超过受害人假如仍然生存在受伤害与死亡期间间本可获得的收入数额。
(八)一般情况下,受伤害较轻的受害人者不能获得任何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某些情形下,受害人遭受到十分严重的极端的身心痛苦并且向加害人提出了侵权之诉时,允许身心痛苦为由要求得到赔偿。出现死亡、严重且永久性致残、毁容或六个月以上丧失行动能力情形时,受害人可以提起因受到身心痛苦之侵权之诉(pains and sufferings)(当然,这些诉讼都受到普通法上所有对侵权之诉的普通时效限制)。即便在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诉诸身心痛苦的请求都必须满足诉讼“起始点”(该提案建议以五千美元为起点),所有低于这一起始点的损害赔偿都不受支持。
(九)统一法案规定的强制保险不仅仅向机动车辆所有者、其家人、其他占用所有人车辆之人和行人提供无过失补偿;而且同时为已保险机动车的所有人和其他合法驾驶人可能引发的对他人的侵权责任提供每人每次事故上限为二万五千美元的保险。如愿意多支付保险费可以得到承保限额更高的保单。[12]
一般而言,这个立法的趋势[13]是朝向无过失的方向。无过失方案的基本内容包含于这个提议之中。
无过失方案的中受到保单保障之对象:其一、保单所载被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的家人;家人指同为居家一处的配偶与子女和其他亲属如被保险人亲属购有另一无过失保险,则不受本无过失保险的保障,避免双重受偿。其二、得到许可驾驶与乘坐机动车之人,许可应是指来自车辆所有人。其三、事故中受到伤害的行人,行人是指车辆以外之人。保障范围的宽泛也是无过失保险与人身意外保险的不同,人身意外险只有被保险人受到保单的保障,而无过失的保障如前所述要广泛得多。[14]
无过失方中的不受到保单保障的对象:其一、事故发生时受到酒精作用影响的驾驶人;其二、事故发生时正驾驶车辆实施犯罪活动或躲避拘捕;其三、自甘风险行为,如从事车辆竞速赛等,己身受有伤害;其四、故意行为导致己身伤害者;其五、未受许可驾驶车辆受由人身伤害者;其六、应购买而未购买无过失保险者。这六种情况中的行为人不得就自己的人身伤害提出赔付请求。
无过失保险给付的项目包括:
其一、医疗费用,包括住院治疗、医疗器械费用、药物费用、手术费用以及康复费用;其二、不能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不超过二百美元;计有收入损失和替代看护费用补偿两大项;[15]其三、死亡的赔付;其四、丧葬费用赔付。
无过失保险求偿的方式则体现了该方案具有的有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的特点。由于采用第一方保险,所以无过失方案中事故发生后的求偿较之第三方保险体系下,,对受害人的利益自然有更多保护。
无过失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和其家属、无论是否乘坐该保单所记载的车辆,只要遭受涉及汽车的事故,无论是以行人还是以同乘人身份卷入事故,都可以依据保单向自己的保险人求偿;也就是说只要购有保单,即使承保车辆没有卷入车祸仍能依据保单受到保障。
货运、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同乘人,驾驶或乘坐雇主提供车辆的驾驶人与受雇人及其家人,向车辆的保险人求偿。
未购有无过失保单,乘坐他人汽车受到伤害,向该车辆保险人求偿。
行人可向任何一辆卷入与自己处于同一事故的车辆的保险人求偿。
无过失机动车保险方案的目的是使得因事故致死或人身伤害获得赔偿更为容易。由于受到伤害的保单持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取代了过去的侵权法诉讼过程,使得获得赔偿变得快捷。在无过失方案中获得人身赔偿的受害人数目会更多,获得的赔偿速度也将较使用传统保险单的传统侵权法体系下大为加快。然而,无过失赔偿方案下获得的补偿数额低于侵权法制度下回复所获得的赔偿数额。
一、 无过失补偿方案的类别
无过失补偿方案的种类主要围绕着对侵权制度的留废程度与人身伤害的经济损失与非经济损失回复两个要点展开。
(一)纯粹式无过失方案
纯粹式无过失方案为第一方保险,保障来自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直接保险合同,保险标的为对车辆事故造成的损害提供综合险保障。提供纯粹式无过失方案的立法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获得保险赔付无需证明事故任何一方的过失;其二、所有的侵权之诉都被废止,受害人不得提起侵权之诉;其三、纯粹无过失方案必定是采强制保险方式;其四、无过失方案必须就受害人的所有因人身伤害引起的医疗支出、康复费用和收入损失等经济损失承担无限制赔付。[16]采此无过失方式最著名的例子是新西兰的事故补偿方案,此方案覆盖的事故不仅仅包括道路上发生的事故而且包括所有领域的意外事件赔偿。
由于无过失方案使得侵权在多多少少程度上被废止,所以即使在最严重的伤害案件中,纯粹的“无过失”方案也必须提供足够的赔偿。(有些可以用)就收入损失的赔偿部分一般要达到满足生活标准线,就起点和上限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再根据残障程度的不同加上有限的非金钱损失的赔偿,纯粹式无过失方案倾向于将主要资源投入到基本补偿和康复两个方面上。
实行这种方案的还有加拿大魁北克省、以色列以及澳大利亚的北部省份。美国没有一个州采用纯粹无过失方式。
(二)混合式(改良式)
混合式方案的补偿数目相对追加式方案更为慷慨。在一些轻微伤害案件中,混合式方案废止了非经济损失的侵权损害赔偿诉权,或是以专门条款防止利用侵权之诉构成双重回复。在另一些法域下,普通法上的诉权以原告有权利获得“无过失”补偿金的限度为界遭到剥夺,已获得补偿金的部分不得享有诉权。美国有十四个州采用了混合(改良)的“无过失”方案。部分“无过失”方案针对经济损失提供了较高的补偿金,已非常接近完全废止侵权制度的纯粹式方案。但是接受补偿金的受害人以获得的补偿金为限失去基于侵权法的诉权;只有在伤害非常严重的案件中,,由原告按照侵权法规则诉请获得赔偿。这种模式被称为“门槛”模式或“起诉标准”模式,各州规定不一,如密歇根州对补偿的给付相当慷慨,对侵权法之诉门槛要求设定很高,因而接近实际上废除了侵权法。
基顿与奥康纳提出的方案就是典型的改良方案。他们的方案是对小额的机动车事故提供一个专门针对它的有限度的无过错适用方案,不管事故由谁引起,车辆相撞中的受害人都能得到包括医疗费和工资损失的补偿。但是除了一些最为严重的事故伤害外,对身心痛苦损害赔偿,即非经济损失,均禁止提起赔偿请求。同时保留侵权法制度,事故受害人所遭受的非经济损失若超过五千美元(作为起始点)可以依据侵权法制度请求赔偿。标准设定分为两种:一种以医疗费用的数量为基数设定排除侵权的门槛,一种以遭受到的身体伤害为标准设定排除侵权法诉讼的门槛。[17]
(三)叠加式无过失方案
叠加式无过失方案是传统侵权责任险与无过失补偿保险并存的方案。在当事人之间不问有无过失保险人径行向受害人支付,受害人仍然保留侵权法上的追偿权利,获得无过失补偿后,受害人仍能够依据侵权法向加害人追偿。叠加式方案的补偿金数额一般低于混合式方案。典型的叠加式方案是以数额有限的无过失补偿金赔付由人身伤害产生的经济损失,但不包括补偿非金钱损失和财产损失的赔偿。这一方案虽不触及侵权制度,但是为避免双重回复无过失保险补偿金与侵权损害赔偿金,就同一损害项目只可就两者取其一。
叠加式又可分为三种[18]:选择性叠加、命令式叠加、强制式叠加。
选择性叠加方案允许无过失保险只是作为购买机动车责任险时的一种选择性添附险种。可以将只是作与普通机动车综合商业险、碰撞险一样自由决定是否购买。此种制度下,保险人有法定义务向投保人提供此保险服务,而投保人没有义务必须选择。
被保险人在事故中遭受人身伤害可向保险人要求医疗、住院及丧葬费用赔付,以及工资收入损失的80%。受害人(被保险人)受领无过失保险赔付不影响其向有过失方提起侵权法诉讼,保险人可按受害人依据侵权法回复得到的金额为限扣除无过失保险赔付的金额。受害人的侵权法诉讼费用自行承担。
命令式叠加是指尽管无过失保险并非强制保险但是一旦机动车所有人购买责任保险就必须同时投保无过失保险;即保险人有法定义务提供,投保人要么同时接受两种保险要么走开。
强制式叠加比命令式叠加更为严格,因为法律要求责任保险为强制保险,而同时责任保险与命令式叠加相同,都附加了无过失保险,因此如果想合法驾驶车辆就必须同时购买两种保险。
(四)选择式无过失方案[19]
针对无过失保险和传统的侵权制度僵持不下立法并存的实际,奥康纳教授提出由机动车保险投保人自己选择的新议案,并得到国会的广泛支持。根据该提议,机动车所有人在购买保险时,可以就赔偿方式在无过失保险方案和侵权法方案之间做出选择。机动车事故发生时,谁可以从谁那里回复损失,同时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本人所获得的保险种类和保单限度以及事故中对方所有的保单的种类和限额。在只涉及保障人身的被保险人(只选择了无过失保险),受到人身伤害的受害人依据自己的保单限额向自己的保险人获得净经济损失赔付,净经济损失超过保单额度的部分可以依照侵权法向受到人身保护的对方要求回复。
如果事故发生在均选择侵权制度的人之间,该法案(议案)则不对此情况发生效力。损害赔偿结果依据侵权法得出。事故如果发生在各选择一种互不相同的制度的两人之间,被保险人首先就净经济损失向自己的保险人以保单额度为限要求赔付。净经济损失超过保单部分中又不属于无形损害的,可以向选择侵权制度的一方要求回复。选择侵权法回复方式者,不能从选择保障人身之人处要求回复无形损害。选择以侵权法回复损害之人的无形损害回复请求只能向自己的保险人依据“保留侵权”(tort maintenance coverage)主张,根据这一保险范围,选此方式的被保险人可以在所购的保单额度范围内回复所有的为侵权法所承认的损害。受到保留侵权保险保护之人还可以就自己受到的净经济损失中超过保留侵权保险保单范围的部分向所有的选择人身保护之人请求回复。
那些选择侵权的人无法向选择人身保护的人回复所有的损失,而且选择侵权的人只能从自己的保留侵权保险中回复无形损害赔偿,而且还必须受到保单限额的限制。这一制度似乎有偏袒选择人身保护方之嫌,因为选择侵权的一方不得不另外从自己的资源中摊出成本抵抗风险。
如前项所述,无过失补偿方案在保险形式上以第一方保险替代原来的第三方保险将传统的机动车责任保险转换为直接存在于保险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补偿损失的保险。尽管无过失补偿方案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仍可总结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向事故受害人提供补偿时不考虑事故任何一方是否存在过失;其次、采用第一方保险;再次、通常仅限于人身伤害补偿、经济损失提供基本的补偿保障。
强制机动车所有人购买第一方(相对于第三方)医疗支出保险为驾驶人与乘客购买收入损失保险。现行无过失保险金仅保障经济损失而不包含精神损害性质的身心痛苦损害。在实行强制第一方无过失保险的州,购买此类保险时申领机动车牌照的前提条件,违反此规定当然伴有刑事责任惩罚并失去驾驶机动车辆上道路的权利。类同于推行绝对强制责任保险的做法。过失驾驶人对受害人侵权法上的责任受到限制。限制的方式通常为两类:一类以受到的伤害程度为标准;一类以伤害造成的医疗支出数额为标准。只有当受害人的合计损失超过一个起始点(thresholds)时才可向侵权人寻求赔偿。各州的起始点不相同。有的州规定依照医疗费用的数目、致害程度的严重性(医学上的损伤或不能工作的天数)或是依照书面要求设定起点(verbal thresholds)。要求较为严格的如密歇根州和纽约州,提起侵权之诉的起始点必须是:重大伤害或严重伤害,包括死亡、下肢截肢、丧失感觉、承重骨骨折;而较宽松的如佛罗里达,只要求构成任何永久性的残疾。
与多数无过失保险方案仅限于提供基本的人身保障这一特征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无过失保险补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财产损失。无过失保险的保障范围一般并不包括财产损失。本文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20]首先人身伤害一般较易引起社会共鸣,为社会多数成员关注,如不受基本的维护唯恐易发生社会问题。另一原因是由于从无过失险的目的出发,保险人被要求迅速向受害人提供补偿,为节约费用一般设置较少调查环节,如此会诱发道德风险。因此包括哥伦比亚方案在内的大多数无过失保险方案仅仅以向事故受害人提供人身伤害赔付为限。而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更多交由商业车辆损失险保险和第三人责任险的财产部分应对。
但是就车辆本身的损失而言,仍有一些立法将其纳入承包的范围。一九七二年马萨诸塞州实施了首个包括财产险的无过失保险方案。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车辆财产损失提供选择性的救济:一种是受保险汽车因碰撞而致倾覆产生损害时,无论被保险人过失有无,保险人扣除自负额度后,负赔偿责任;一种是受保险汽车受有损害时,被保险人须就此项损害系由加害汽车驾驶人之过失所导致提供相当程度之证明后,保险人始于扣除自负额后为赔偿;另一种是对于受保险车辆不提供保险,被保险人也不得对被保险人提供任何赔偿请求,但可在法定责任范围内免除其对外的侵权责任。
对财产保险规定更为彻底的密歇根州则在财产险中完全废除侵权责任。传统侵权法上因对车辆的所有、维护和使用所导致的全部财产损失的侵权损害赔偿都被取消,代之以责任保险和第一方保险并举的庞大投保范围。车辆所有人被要求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同时被要求为自己的车辆损失投保无过失第一方保险,第一方保险的赔付额度最高为一百万美元。可在上面提及的三种类型的条款中作选择。并且该州责任险和财产险均为强制投保。,代之以无过失赔付,这一来自制定法的废止合理地涉及了宪法许可的制定法立法目的,并不违反宪法“正当程序原则”,同时无过失财产赔付限额对保险人负担的绝对责任的课以限度,从精算的角度看属于妥当,并不违反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密歇根州司法威权对此在财产赔偿上比起传统侵权法权利的方案的合宪性予以了首肯。[21]
车辆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分为三种类型。车辆相互碰撞因此产生的车辆损失、车辆撞击静止物体后造成车辆的损失和造成物体的损失。有建议提出汽车保险应当对被保险人车辆与其他车辆相撞受到的损失,不论事故过失处于何方,保险人应当对向其投保的被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获得自己的保险人的赔付后失去向加害人的追偿权利,同时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之后不能向加入了无过失保险方案的加害人要求赔偿。这类方案属于典型的第一方保险并课以强制保险方式,法律关系直接存于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按,事故发生后的理赔属于垂直式赔付方便快捷,在赔付时也不考虑事故的过失排除侵权法的适用。但是由于涉及单车事故,[22]不免会产生道德风险之虞。
二
这些制度和看法的不同背后隐藏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有必要介绍一些基础理论的探讨,本文不作深入讨论。对于意外事故的态度。事故不可能完全消除,那样做代价太大,加多·加拉布拉西(Guido Calabresi)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事故发生存在一个“最优”程度;法律要做的是减少而不是消除事故。下一个考虑是,事故引起的代价是否公平的分布,在什么是公平的问题上人们见仁见智,有人看重的是经济损失要广泛散布不能让个人承受,有人则坚持:由引起事故的人承担责任才是公平。关于法律对赔偿的目标,学者们一直以来有不同的理解。存在道德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经济分析理论、权利说理论。真实世界的法律制度尽管并不能完全地无折扣地体现这些理论所蕴含的主张,但是这些理论通过学者的鼓吹和游说集团施加压力所必须的借助利用的,已经对现实世界的法律涉及产生了影响。一、道德理论。道德理论一贯是传统的侵权法理论的主张,其核心建立在个人道义责任这一概念之上。这一理论蕴含着这样的涵义,一方面,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无可避免地不断给自己和他人制造出风险,自己必须学会运用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应对自己和别人相互施加的风险,比如通过储蓄或是保险来应对;另一方面,一旦由于道义上不负责任的行为举止引起了损害,冒犯他人之人就应当为此赔偿。二、分配正义理论。分配正义理论刺激了二十世纪的福利式立法,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分配正义理论又为侵权法理论家采用作解释和鼓励将人身伤害和死亡案件的责任承担加以社会化的理论依据。由于一些引起意外伤害的活动本身是有利于社会整体,由未受到伤害同时又从引起意外的这类活动中获益的社会成员分担损失就似乎很了一种公平的选择。实现的方式可以是采用集中化的无过失的补偿方案,或是采用对那些能够通过保险或是自我保险(即,通过产品或是服务的定价)移转损失负担的成员施加责任,后一种即被称为侵权法的“损失分布”功能。而分配理论本身又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将赔偿这种分配资源的方式看作是对社会和经济上被剥夺权利、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刻意的保护,避免社会成员中最无法抵御风险的群体或个人落入不利,这是一种分配资源上的反向调拨。而另一种解释并不区分受害人的财富状况。分配理论对于人身伤害的赔偿具有十分深远重大的影响,然而出了这一领域,此理论的影响力却值得怀疑。在无过失补偿立法中往往更多的体现了前一种解释,即关注于使得最弱势群体免于由事故带来的绝境为受害人提供回到基本的社会生活提供保障。三、权利理论。权利理论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权利论者强烈反对由于某些引起损失的活动本身有利于公共利益就忽略了引发并施加这些损失带来的问题。权利论者提出了一套规范性的概念,强调个人自主,他们特别选出一些属于人类的人身性要素作为衡量尺度,要求对于自由、肢体完整、尊严等要素予以特别程度的保护。持有这派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这些利益的主张高过其他的权利与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侵犯即使加害者本身并不具有过错,仍然应当产生责任。这些理论主张在人身伤害赔偿中得到了响应。
人身伤害领域内的赔偿观念在制度上体现着这些赔偿目的观视角的是四种模式:[23](1) 由诉讼为驱动以过错为基础的赔偿(lawsuit-driven, fault-based compensation);(2) 以事故代价内部化注重赔偿的方案(accident-cost-internalizing, focused compensation plans);(3) 配以政府管制的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 paired with government regulation);以及(4) 市场(the market)。大多数社会的制度安排不是纯粹取其一,而是将这些模式的要素以自己的特别方式组合而成。尽管如此,这些模式本身反映着彼此间明显不同的政策。
模式一是传统的以过错为责任基础的法律,普通法与大陆法都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这一模式。它要求以金钱惩罚来起到威慑效果,要求行为人作出适当预防,尽到“应当的注意”义务,这一策略可以用来避免那些可合理避免的事故(reasonably avoidable accidents),而将那些难以有效率避免(not efficiently avoidable)的事故其引起的代价交由受害人承担。受害人可以通过事先安排私人保险来支付损失。[24]实践中,以过失为基础的侵权未能完全有效的阻遏所有的可合理避免的事故发生。所以行为人未尽合理预防致他人损害,受害人可起诉过失方,将事故引发之费用转移于未尽合理预防的加害人。这一方法确信司法过程能够在事后确定损害的风险是否为不合理地施加。
模式二的典型是带有严格责任色彩的劳工赔偿制度。大型组织(一般是商业企业)被要求,对落入自己领域内的风险进行管理,并要对由此发生的事故进行赔偿,而不问其是否有过错。。这一模式的正当性在于认为组织有能力从这些需要它负责的领域中获益,受害者也可从扩散损失的体制中获利,而不用另行安排私人保险。这一模式将所有的事故费用(包括)交由大型企业负担,这样的安排会激励这些组织做出有利于社会的预防。劳工赔偿与极度危险行为(extra-hazardous activities)中适用的严格责任反映了这一特征。道路事故交通领域的无过失补偿设想最初来源于劳工赔偿制度。
模式三中,政府通过独立的机构直接就事故优化与赔偿目的承担责任。政府的安全部门采用管制方式设计一定水平预防措施,同时政府的保险机制提供受害人赔偿。,他们通过事先(ex ante)设立行为标准充当中立的专家身份。这一点是与模式一的区别,在模式一中政府以司法制度面目出现,以事后地(ex post)适用概括性的过错标准判决赔偿。
与模式二不同的是,模式三中社会保险制度的资金筹集不区分可能发生损害的领域的危险大小,而是从一个广泛的收入来源中获取资金,而与不同特定的组织中事故发生水平相联系。与之相反,在模式二中,赔偿资金来自特定组织并限于特定领域进行赔偿,这种费用的内部化(cost internalization)恰恰是促进安全的金钱激励。不同于模式二之处还在于模式三的事故受害者没有被单独区分对待,他们在健康医疗和基本工资等方面与其他公民一样受政府提供的安全网的保护。,,并保证了对受害人提供了赔偿。目前实施无过失保险立法的国家都将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范围视为由立法部门决定的事项。模式四要求私人承担预防自己受到损害的义务。如果由他人承担预防会更好的话,这些预防会通过市场的方式解决。这意味着产品与服务的买卖双方通过约定将在自愿交易中采用的预防措施,来共同管理风险。它假定了应由个人而非法庭、政府机构或大型组织决定该冒何种风险,何种风险应该以风险预防的名义减少。这一模式相信市场的能力,私人将自行决定风险分配,政府的角色退位到执行私人间的契约安排。模式四与模式二一样只能适用于部分领域,在诸如机动车事故和“陌生人”间发生的伤害中,由于缺乏交易过程而难以适用。
:保守主义conservative(s);自由主义liberal(s);公有至上论communitarian(s);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s)。传统的普通法上的侵权法之诉,属于具有保守性格的制度。它强调为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的个人责任,既赋予应获得救助的受害方以个别的救济权,又要求受害人自行承担不能归咎于他人的损害。通过这种威慑性阻遏惩罚,希望人们能自行认真对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使得政府不需要进行干预。只有当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针对另一方行使诉权时,政府的作用才触发。这一制度能最小化行政官僚机构的作用。模式二体现了当代的自由价值观。这一社会意识形态引导向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个人过错并不重要,社会中大制度的力量被看成是关键因素。自由主义观点强调“大致的正义”(“rough justice”)而非输家赢家分明、精致且代价高昂的个体正义(individual justice)。在制度上他们要求政府强令大型私人组织负担公共目的。模式三认为事故的代价要分散为社会承担。因事故致残的命运可能落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上,社会必须为那些暂时或永久致残的人提供相当的医疗与相关服务以及替代收入。同时他们认为社会成员应自觉地设立行为的准则,当有风险或损害发生或处于危急关头,降低风险是首要之事。他们认为个人有义务参加自治集体。模式四体现了自由至上论的价值观,怀疑政府的干预信任个人选择。他们认为政府一般应该把手从试图控制公民行为上拿开。应该允许个人经营自己的风险,政府不需要干预。占主导性的价值是自由,自由至上主义者高度看重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在保持与促进自由上的作用。
自机动车发明问世以来,对于机动车所造成的事故,法律大致采取的做法恰都或多或少纯度不同地体现了这四种理论。最早期仅仅凭借侵权法单一制度并适用过错归责、完全交由司法部门裁判的处理方式体现的正是传统的模式一;之后引入目的完全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赔偿损失后被保险人损失的早期责任保险,试图以市场的方式解决赔偿问题也体现了模式四中的市场为主排除政府行政式计划式干预的主张;之后法律进一步承认了受害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诉权,法律为了提供更为广泛的保障更进一步实施了强制第三人责任保险,这些变化体现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在保险制度上对危险制造一方要求更为严格,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这表明在强制责任保险大行其道的时期,法律尽管仍然保留了模式一的诉讼处理模式,但是已经逐渐在弱化并逐次否定模式四的理论主张。
存在强制责任保险这一事实使得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英国的法官在审理机动车造成人身侵害时越来越多地考虑给予慷慨赔偿,因而在引起人身伤害赔偿的机动车事故中,,而采用实质的或接近于无过失归责的解释。在这些国家,法律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分担的看法始终没有放弃模式一的处理方式,但是逐渐地吸纳了模式二与模式三的主张将严格责任和福利国家观念注入制度设计中。
而另一些普通法国家则依靠采用另一类保险形式作为工具试图抛开侵权法或是最大程度限制侵权法在赔偿中发生作用。也就是采用了无过失保险方案,由于这些方案具有保障范围宽广、赔付迅捷的特征,正体现了福利国家理念的诉求。但是这些立法措施同时意味着全部(采用纯粹式无过失方案)或部分地放弃了模式一坚持的诉讼方式,转向一个更为接近社会保障的制度,由集中化的机构运行管理、处理赔付,赔付的种类由制定法规定、按统一方式计算。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针对机动车事故领域的赔偿现代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发展越来越注重降低受害人获得人身损害赔偿的难度,注重通过社会整体范围内分布的方式实现风险后果的消解。对于人身完整与尊严等权利的维护也被置于法律的优先地位。
三
笔者的看法是,侵权法的逻辑落于矫正正义,这种思路对危险的观点是:危险带来的损失应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分配,这就是矫正正义,是私法的逻辑,损失以你来我往的方式来回分担,[25]这是在直接与风险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之间来回转移风险。但社会保险的思路是分配正义的思路,它是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外的人之间分布损害,不是刻意在两方之间来回,而是要将整个水泼出去,是扩散损失将损失在超出直接与风险相关的利益相关人的更为广大的人群之间分布,易致损害的风险由多样的人承受,这些人从风险中得益的机会、比例应该是趋向于同等地多或少,因而他们应该同等地被置于风险之下。
在侵权法制度语境中,事故中的侵权归责原则(principles of responsibility)无非是适用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或是过失(negligence)之争。前者主张无论侵害人施加的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风险负担(reasonable or unreasonable risk impositions),都要承担事故发生的责任;后者主张侵害人仅对施加不合理的风险负担所引起的事故承担责任。美国法上主要的见解是危险活动致害的归则原则适用后者,因而带来第二个问题“风险负担何时是合理的?”理论上往往这样看,侵权责任设置要把事故的代价与预防看成一个整体,从社会的角度尽量减少这个整体的资源消耗;另一个角度是侵权制度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天赋权利,每个人都有维护人身完整不受侵犯的自然权利,使我们免于遭受他人施加的伤害。这样又要求事故法的设计必须是有事先的同意才可施加风险,事后的损害赔偿作为事故伤害的代价。[26]
折中的看法是要保留普通法的侵权制度,但要伴之以较低保障程度的社会保险性质的人身伤害补偿方案。用社会保险的方式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保留部分的普通法下的救济请求项,如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等。
侵权制度下要求保留过失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要件,侵权法坚持对人身伤害带来的非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而无过失补偿方案则排除因人身伤害带来的非经济损失补偿。
侵权法所体现的矫正正义必然暗含着因果关系。它要求凡符合矫正正义的两个事件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而分配正义并没有要求必须在资源的失去者和资源的付出者之间有导致这种财产变动的引致因素。甲的所失可以来源于乙的所得,但是却没有一个具体的事实上的联结点完成这个财富移转的链条。
传统之见是将无过失方案的正当性建立在分配正义之上,而将侵权法体系的正当性建立在矫正正义之上;两种做法皆出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探讨所使用的概念。矫正正义需要在财产变动的成员之间发生某种因果关系,财富由甲到乙的流动,甲和乙之间必须要建立某个特定联系,使财富在两者间的转移具有正当性,这个联系是符合矫正正义的必要条件。侵权法完全是在遵循这个要求,侵权法从来就是事关私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领域内的矫正与回复。而分配正义更着力于财富在一个群体内的分布,并不再以每一个财富的移转是否有明确的因果关联作为财富移转的正当化的前提。无过失补偿方案具有这一特征。
从法律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就实际制度的目标及其实现情况可简要归纳为,无过失补偿方案的最大优势是可以提供侵权制度所难以提供的、为所有遭受身体伤害之人提供补偿;而侵权制度之根本优势是,能够提供阻遏功能并且可以要求实际加害人(行为人)的承担责任(问责落于个人),这点同样也是无过失补偿制度所不具备的。无过失方案的最佳之处在于事故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都可以得到补偿,而侵权法的最佳之处在于具有阻遏功能以及能使行为人个人自负其责。[27]
无过失保险方案胜过以过错为基础的侵权法的最佳理由是能确保所有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基本的经济损失补偿,针对经济损失实行有多少损失填补多少损失的原则,就受害人获得的赔偿而言较为均衡,倾向于不发生侵权制度下轻微伤害赔付过多、严重伤害又赔付过少的不均衡欠公平的弊端,在人身伤害赔偿上尤其更能体现出无过失方案此处优势。其次,由于实行垂直赔付一般不需要调查事故中的过错因素,所以较之与过失侵权体制同时运作的责任保险,其运行费用更低,赔付的标准有指定法作为参照指导,因而较之采用交叉理赔并需要保险人调查、抗辩并和解的责任险为短。[28]再次、节省获得补偿的时间,由于采用分期式发放受害人专门获得医疗康复的可能得到了稳定保障。[29]
有一种担心由于无过失补偿制度取消身心痛苦等精神损害赔偿,导致律师对代理受害人的兴趣降低,以至于受害人会因此缺少称职的法律服务,这种忧虑是仅仅站在专门从事诉讼的律师的角度看问题得出的观点。采用无过失补偿后,事情从本质上看仅仅是使得原本由专事诉讼的律师承接的业务转而由从事事务性工作的非讼律师接管而已,并不会造成法律服务的真空。
另一项无过失保险相对责任保险的优势是其保单的保障能力较后者强。尽管强制责任保险在保单限额内也承担无过失责任,但是一般而言责任保险保单的解释是针对每名潜在受害人设定一个保险金赔付额度,同时又对一起事故本身设有最高的赔付额度限制,如事故中的受害人较多则受害人必须于最高额度内分享保险金;而在无过失保险,由于保障受害人的保单仅仅就受保单保障之人每人设定了最高额赔付标准,无另设事故最高额限制,无论多少人在事故中受有伤害,保险人按照每一人的保障范围为给付。[30]所以在无过失保险下,保障较为可预期、稳定可依赖,这也是无过失补偿方案立法目标中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目标的体现。
无过失方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逐渐在不同的国家中实施。这些程度、范围不同的无过错补偿方案也自那时起,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争论与探讨。通过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和学者的经验调查,今日的人们发现侵权制度与无过失补偿两个制度都存在有一定的缺陷、都面临一些难题。一些欧洲国家试图同时将两种制度调和适用在交通事故领域内,即将严格责任和无过失保险补偿制度并存,这种尝试也产生了问题。以瑞典一九七八年《交通损害赔偿法》为例,该法将两个制度整合到一个单一的赔偿制度安排中去,无过失保险补偿并不排除在保险中适用侵权法原则。该制度中决定赔偿数额的原则来自侵权法规则,法律要求受害人必须依据侵权法的规则获得完全的赔偿,确保赔偿足以使得受害人恢复到如同事故未曾发生过的以前状况。而保险人被要求按照适用侵权法严格责任得出的数额向受害人支付。[31]
从法律制度设计面临的社会费用约束来看,要保有两套制度就会有两重法律上的制度安排:一面是社会性的法,类似于公法,其性质上属于汇集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的带有行政色彩的制度安排,另一面又有传统上私法性的由司法提供救济;这里会要求有解释、调和、界分这两种法律(广义)辖权的费用存在,这些专门知识维系所需的费用高昂而生产出所求的难度艰巨,又加之公法性的制度安排会受制于由民主制度下的立法活动所带来的震荡与反复,如新西兰较晚近的动向是缩小了其事故赔偿的范围,[32]这似乎是民主制度下的不能预测的立法机关变动的直接的例子。相较之下,司法不是强调民主的制度,从制度分工上她就是一个不必屈从于多数的、流行甚或主导性意见、风潮与见解的场所,她展现的往往是少数人的智识,她保守地应对变动不居的现象,这既是暗示司法制度与立法活动并存,如欠缺程度必要清晰的界分将会带来法律设计的冲突又暗示也许司法制度传统上的优点,或说是中立一些,其固有的特征(保守且不屈从流行与多数)会带来法律的稳定与可预测,兼之对这类伤害的救济牵涉到对人的基本权利(身体完整等)的保护,将救济的最后诉求(final resort)留给司法这个依赖智识而不是人数的机构,。无论如何,如果制度是这样的,为了保有这个设计,社会将负担双份费用。这其中的道理与权力分离的理由是相近的:有时候为了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进了一个篮子的风险,我们不得不人为地增加提供一项公共物品(服务)的费用。
当然,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如何是验证的工作(empirical study),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实值参考,[33]本文只是作了粗浅的理论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而无疑,设计出色的验证工作才是真正的试金石,经验数据会推翻似是而非的理论。
四
最后,引用一段欧洲法律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为归纳和小结:一方面,显然侵权制度无法独自对人身伤害补偿的问题提交令人充分满意的答案,为确保个人不会因遭受人身伤害而从经济上被毁掉,那么社会保险、商业保险肯定是侵权法制度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完全废除侵权法不可行,因为需要制度设计中必须保留个人承担责任的因素存在,个人的责任有助于增加潜在侵权人与潜在受害人避免损失的动力诱因,只要侵权制度存在,对两方就都存在激励,侵权人惧怕天价赔偿,受害人唯恐获赔不足,所以都会产生避免意外的动力,提高预防能力。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的过错已经不是责任承担的首要理由,责任承担的主要理由是引起了日渐增长的风险。谁施加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对现实化了的风险造成的损害施加金钱性的制裁,从欧洲的角度特别是从德国的角度,问题的一面是社会保险与私人保险的相互协调,另一面是保存侵权法制度仍属需要,如在涉及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场合出于报复(目的)而施加惩罚的目标又会抬头,而且在阻遏与防止上侵权法又以经济上的诱因为外衣重获重要性上的考量。[34]笔者以为,这是对一般性问题的回答,同时也适用作对道路交通事故领域的看法。
【作者简介】
蒋天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任职。
【注释】
[1] 批评的理由:针对普通法的批评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于人身伤害案件,普通法的唯一救济方式是一次性支付赔偿金。而对于诸如收入能力的缩减或今后的医疗支出等未来的损失而言,这是不适当的赔偿方式。赔偿金额在开庭时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即使之后受害人方的情势发生急剧且不可预知的变化,赔偿决定也不可更改。即使法官们自己也加入了对这种做法的批评之中。因为在通货膨胀环境下,让法庭就普通法上人身伤害诉讼损害赔偿数目做出衡量是一件对法官勉为其难的事情。法官、保险人及其他法律实务工作者不得不去预测诸如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受害人的预期寿命、今后的就业前景等不可能预估的问题,那些卓越的法官也承认:至少在严重伤害的案件中,估计损害的处理方法经常是武断的,因而建议立法上的改革是必需之举。See 2.4-2.5 和Issues Paper 2 Outline (1982) - Accident Compensation Why is an Inquiry Timely?
THE DISCOUNT RATE 贴现率。这方面澳大利亚的先例是Todorovic v. Waller (1981) 56 ALJR 59,就人身伤害诉讼的一次性支付赔偿的估算上这是一个援用的案例。这是一个数学上的方法来决定未来经济上损失的现值。这里的逻辑是“给定一个数目的货币,其在手头的价值高过日后得到同等数目货币” Todorovic v. Waller (1981) 56 ALJR 59, at p.62. 在该案中个别法官提出贴现率在0%到5%,而大多数法官同意折衷为3%。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中的两位(Chief Justice Gibbs and Mr. Justice Wilson)认为,估算损失中的计算“远离实际”,他们所作的决定十分武断。必须通过立法来确立社会政策。在Barrell Insurances Case (1981) 34 ALR 162一案中,Mr. Justice Stephen 说一次性支付赔偿会产生不希望的后果,比如导致不适当的高保险费,而外国的模式是用立法上不依赖一次性支付的补偿计划来救济。他进而指出依照现行法,不管依据预计作出的一次性支付赔偿后来显得错得多离谱,决定不可更改。他说,这一缺陷只有通过“根本性的立法干预”来克服。
赞同的理由是:与之针锋相对:对普通法的支持理由:
侵权制度已为社会所认同接受理解。普通人已接受人应该为自己的过失向由其过失造成伤害之人赔付所有的损失。责任保险制度广泛实施也没有改变这一原理带来的智识上的说服力。
普通法上的诉讼仍具有威慑阻遏功能,比如,侵权法制度能曝光欠缺安全性的工作惯例。雇主或是其他被告如果疏于预防未能防止事故发生将会导致自己的保险费率上升,因为普通法的诉讼审理结果能得出结论他们一方存有过错。普通法会围绕过错进行审理,而无过过失制度是不管这些的。
普通法诉讼是唯一不是根据一个规定好的计算标准而是依据原告的个案情况衡量赔偿额度的制度,这样更能通过保有灵活性实现正义。
普通法诉讼时交由法庭而不是行政部门决定赔偿请求的命运,。
一次性赔偿判决具有巨大的价值。这种方式对赔偿请求权作了处分促进了诉讼中的终局性,剔除了持续的不确定性使原告可面临的选择得以最大化。相对于只要权利人不能恢复工作就按固定时间逐次给付的方式而言,一次性赔付更有利于促进受害人康复。
[2] John G. Fleming: The Law of Torts, (Sydney,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1983).
[3]E.W. Hitcham: Some Insurance Aspects, in The Law of Tort: Policies and Trends in Liability for Damage to Property and Economic Loss, Michael Furmston Edits. Duckworth, 1986, p192.
[4]Western Suburbs Hospital v Curry (1987) 9 NSWLR 511.
[5]较为激进的做法是在采取无过失主义归责同时对因果关系也放松要求采相当因果关系甚至对事故损害引起的人身伤害取消因果关系要件证明。、甚至不考虑因果关系的主张。Bill W. Dufwa: Strict Liability in Tort Law, Colloque international à la mémoire de Jean Limpens (Gand, 22-23 mars 1984).
[6]见W.L. Prosser,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 (West Publishing Co., 1971), 558.
[7]见Clarence Morris and C. Robert Morris, Morris on Torts, (Minneola. N.Y.,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80), 245
[8]见Clarence Morris and C. Robert Morris, Morris on Torts, 244-255.
[9]Doug Bandow: Auto Insurance Needs “Auto Choice” 一文指出,根据兰德公司的公民正义报告:除了老生常谈的受害人迟迟难得赔偿外,受损害不足5,000美元的人,往往得到高出实际经济损失二至三倍的赔偿,而损害在25,000至100,000的人得到的赔偿不足实际经济损失的一半。损失数额更大的人能得到的则不足9%。得益并得意的是律师,诉讼中真正的赢家。为身体伤害承包的保费中的40%落入了律师的腰包。原被告的律师都应对此负责,原告方的律师只要有可能就诉求采取求得判决而不是调解的策略,而被告方律师往往采用拖延策略,这样诉讼所需的费用大涨,在十五个采用各种版本的无过失方案的州里,情况要好,因为事故赔偿途径方式不需面对诉讼律师而是由经营的保险公司公司对自己的主顾进行赔偿。Michael Horowitz和Jeffrey O“Connell认为应当给当事人自己选,是选择目前的侵权法制度还是选择所谓的用于保护个人的保险(personal protection insurance, PPI),选择后者的从自己的保险人那里获得经济补偿他们就要放弃普通法上对非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的权利(尤其要放弃精神损害的赔偿)。
[10]F.H. Lawson and B.S. Markesinis: Tortious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Harm i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 Volm.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4.
[11]在真正工业化时代的许多导致意外事件发生的场合中,原先建立在教谕和道德上的“过错”概念根本无法从中找到用以架构认知事物、分析事物的意义,许多意外事件的促成含多种因素,当事人在其中只有出差错的行动而非具有过错性质的行为。,在一项由一群以往记录良好具有经验的机动车驾驶人参与的经验性测试中,每位驾驶人在五分钟内所犯的错误超过九个,且来自多种不同性质的错误,而在此测试前的四年间并没有任何该驾驶人的事故记录。传统上的“过错”的概念是假设了存在一种行为人做出的选择,被称作是具有过错的行为是一种选择之下的不当的行为。然而,司法活动中认定的过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指“经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无法避免的结果。由于人类的反应和生理、心理能力是有限度的,在压力和刺激下的行为其实更接近一种动作或是举措,而非有加害动机或意图(无论是过失还是故意)的行为,它们应当被看作是从事一种合法活动所不可避免也无法避免的结果。见F.H. Lawson and B.S. Markesinis: Tortious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Harm i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 Volm.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44-45.
[12]见Clarence Morris and C. Robert Morris, Morris on Torts, (Foundation Press, 1980) pp246-247.
[13]趋势,是一个对现象的解释。在属性上,趋势本身不可能是一个事实,但它是对现存事实及出于某种理由相信现存事实会延续下去而产生的从现存事实导引出的事实的描述与解释。因而,趋势的性质是某种理论,是一种对事实的解释。困难在于,我们对于过去的观察,以及基于观察之上的解释(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又有助于我们对趋势做出尝试性的描述呢?出于描述的困难,与之相应的解释的困难,我只能假设当过去的条件出现时,从类比中,我们可以建立起对假设中的未来事件的解释(描述)。关于法律的趋势,指对属于法律的制度和做法的将延续,所做的预期与对这种预期的解释。本文难以以这种方式进行探讨。本文只能为进一步的这类探讨提供一些背景,制度特征与理论发展的铺垫。特此予以说明。
[14]无过失保险与人身意外保险的另两个不同在于,前者通常不包括精神损害赔付并且只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
[15]看护费用包括:由于受到人身伤害而不能对家人或有供给关系的人提供原来可以提供的服务的损失以及雇用他人代为提供这种照顾服务所需的费用。收入损失则包括劳工补偿、社会保障补偿、社会保险补偿等。
[16]由于采用分期式支付方式,受害人尽管不需证明事故中加害人的过失。但是有义务分阶段证明本人在受伤害后仍应当继续获得经济损失项下的赔付。
[17]见上文第二章第二节第三项。
[18]施文森 著:《保险法论文(第二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64—265页。
[19]James A. Henderson, Jr., Richard N. Person and John A. Siliciano, The Torts Process, 6thed. Aspen Publisher Inco. and CITIC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643-44.
[20]恩格兰德指出有两个原因,其一人身伤害召唤社会连带性。肢体的生理损伤被认为是集体性的责任,在福利国家里,个人的身体完整性被当作是社会集体必须相互承担的责任,而现代社会的思潮认为一旦个人由于事故受到了肢体不全的不幸,应当有权利从集体中获得补偿。其二,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相对而言较容易进行,交由集体性的保险处理更为妥当。事故发生前的收入可知、未来的收入可以按照其具体职业或行业分支依据统计得出详细数目,无论是金钱性和非金钱性损害赔偿额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客观标准加以标准化设计,如有必要还可以对一些赔偿依据合理的平均数设定封顶的额度。而财产损失本身不像人身损害那样易于确定,不易于无过失保险处理,也因为可能引起道德风险的机会存在,因而交由保险公司以第三人责任险的方式处理为佳。
[21]施文森 著:《保险法论文(第二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89页。
[22]指只涉及一辆机动车的事故,比如开车撞击路边砖墙。
[23]Stephen D. Sugarman, Personal Injury and Social Policy: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Alternatives, published in “Torts Tomorrow: A Tribute to John Fleming” N. Mullany and A. Linden, eds. The Law Book Company, 1998.
[24]参见GREGORY C. KEATING: FAIRNESS AND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THE TORT LAW OF ACCIDENTS, Olin Working Paper No. 99-21,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School.
[25]B.A.Hepple and M.H.Matthews: Tort: Cases and Materials (London, Butterworths, 1985), p768.
[26] Gregory C. Keating, Fairness and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the Tort Law of Accidents, Olin Working Paper No. 99-21,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School Los Angeles, CA 90089-0071)
[27] Hassan El Menyawi, Public Tort Liability: An Alternative to Tort Liability and No-fault Compensation,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ume 9 Number 4, 2002 Dec.
[28]根据加里·施瓦茨教授的论文,在实际的保险业运行中,无过失保险保险人有渠道获得事故的因果关系而无须花费额外高昂费用。通常以警方的事故调查记录为参考。保险人也可以通过模拟责任保险所采用的“无诉讼奖励”的方式,根据投保人的驾驶记录和事故记录等对不同的驾驶人收取不同水平的保费,取得激励驾驶人谨慎驾驶促使保险运行费用降低的效果,也将扼制保费的上涨。See, Gary Schwartz: Auto No-Fault and First-Party Insuranc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0, (Vol. 73): 611, 643.
[29]Glanville Williams and B.A. Hepple: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Tort, Butterworths, London, 1984, p194.
[30]施文森 著:《保险法论文(第二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76-277页。
[31]Bill W. Dufwa: Strict Liability in Tort Law, Colloque international à la mémoire de Jean Limpens (Gand, 22-23 mars 1984),这种混合无过失方案和严格责任的做法,由于规则过于复杂导致不甚清晰,而受到批评。详见本注所揭文注64。
[32]Stephen Todd: Privatization of Accident Compensation: Policy and Politics in New Zealand,Washburn Law Journal (Vol. 39) 2000,404. 新西兰的事故补偿方案覆盖所有因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是最为综合性的方案。专设机构管理基金并负责处理有关受到伤害之人的补偿申请。该基金的融资来源是雇主、汽车所有人和其他有义务缴纳费用的人。一九七四年新西兰此举为天下之先,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经重大变更,为降低运行费用方案覆盖范围受到缩减。
[33]根据经验调查的数据:就机动车无过失保险对致死事故发生率的影响所做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他们的分析表明限制受害人的普通法上的诉权会削弱谨慎驾驶的激励,导致更高的事故发生率。经分析了1968-1996全美各州机动车事故致死率的数据,这项经验研究表明无过失制度与较高的致死事故率的相关程度高于侵权制度。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不能两全的取舍,无过失制度相较侵权有优点但会加剧致死事故的发生率。但加强经验等级制度将事故发生之前纪录良好者的抚恤金数目提高也许是一项解决办法。See,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NO FAULT AUTOMOBILE INSURANCE, February 26, 2001 本文后附有一表格显示另一项经验调查结论;Peter Sheldon: NO FAULT vs. TORT INSURANCE SCHEMES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eptember 27th, 1996.
[34]Ulrich Magnus: Compensation for Personal Injur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362 Washburn Law Journal Vol. 39
推荐阅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
最新资讯
-
08-11 1
-
08-06 2
-
08-27 1
-
08-23 2
-
08-04 1
-
12-2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