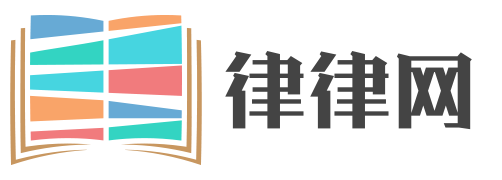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若干问题之思考
发布时间:2020-08-07 01:22:15
内容摘要:代表诉讼提起权是股东的一项重要权利。该项权利若能行使得当,则对公司利益的维护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大有裨益。为了充分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功能,我国在导入该制度时,既要设计出预防原告股东滥诉的适当机制,如代表诉讼原告资格、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以及败诉原告股东的责任等,又要采取相关措施激活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如强化胜诉股东的费用补偿请求权、比例性个别赔偿请求权等。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 原告股东 公司利益
公司利益是股东、债权人和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当公司利益受到侵害时,公司机关应及时行使公司诉权,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挽回公司的利益损失。但在公司实务中,公司机关的组成人员,如大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等本身往往就是公司利益的侵害者,或者这些人员与公司侵害者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在此情形下,势必会造成公司诉权行使之懈怠或不能。基于此,英美两国率先创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随后很多国家纷纷效仿。所谓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当公司拒绝或怠于向侵害公司利益的加害人提起诉讼以诉求司法救济时,公司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位公司起诉,以追究加害人的责任,维护公司利益的一种诉讼制度⑴。时至今日,该制度在国外已成为广大股东监督公司经营及预防经营权滥用的最重要的救济和预防手段。而我国,由于公司立法经验不足,《公司法》尚未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笔者认为,为了更周全地保护公司利益免受各种不当行为的侵害,我国公司法应旗帜鲜明地保护股东代表诉讼权利。
一、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范围
代表诉讼提起权是每个股东都享有的一项股东权,将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范围限定为股东,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立法采用的原则。但笔者认为,我国代表诉讼制度中原告不应理解为狭义的股东。
原告股东,既可是记名股东,也可是无记名股东。在日本,有学者认为代表诉讼的原告只限于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在1962年到1982年间也曾要求原告是其起诉的不正当行为发生时的记名股东,但后来美国公司法不再将原告局限于记名股东。如目前《美国模范商事公司法》第7.40条明确规定,“股东”一词包括那些将其股份设立表决权信托、或者指定第三人代表自己持有股份的受益所有人。《纽约公司法》第626条第1项也将代表诉讼的原告界定为“股份持有人、表决权信托证书持有人或者对于此种股份、表决权信托证书拥有信托利益的当事人”。这主要由于当今美国有许多投资者以证券商名义购买股票,或者通过机构投资者购买,并大量运用表决权信托制度。将这些股东排斥于代表诉讼制度实属不公。笔者认为我国导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时,原告也应包括表决权信托证书持有人以及对于股份或者表决权信托证书拥有信托利益的当事人。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我国香港公司法属于英美法系,我国入世后将有更多英美法系的投资者加入我国股东行列,且我国已有公司在香港和国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至于可转换公司债的持有人和股票的质押权人是否具备提起代表诉讼的资格,笔者认为:(1)可转换公司债的持有人不同于普通公司债的持有人,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潜在的公司股东。若法律机械的规定,“可转换公司债的持有人在将其持有公司债转换为股票后方可具备提起代表诉讼的资格”,那么,在可转换公司债的转换条件成就之前,公司被侵害后产生的诉权有可能因罹于诉讼时效而消灭。这既不利于公司利益之维护,也不利于可转换公司债的持有人利益之维护。故可转换公司债持有人应具备提起代表诉讼的资格。(2)股票的质押权人也可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提起代表诉讼。此条件大致有三项:一是债务人股东具备提起代表诉讼的诸种资格;二是股票质押权人的债权已经逾期且未得实现;三是股票质押权人提起代表诉讼时应诚实守信,无恶意。⑵
另外,原告股东的(概括)继承人也应在原告范围之列。若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后消灭(法人股东)或死亡(自然人股东),则法人股东的概括继承人或自然人股东的继承人可以继续维持代表诉讼。因为股东的(概括)继承人在取得股份后,就变成作为真正原告的公司的新股东,与代表诉讼当然存在着间接利害关系。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
(一)原告持股时间的限制
美国《模范公司法》和许多州的公司法均采用“当时股份拥有”规则。《模范公司法》第7.41条第1项将该规则界定为:提起和维持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必须在起诉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发生时具有股东资格,或者由于法律的作用从此时的股东取得股东资格。例如继承人对于股份的取得,就属于法律作用之结果。采取该规则的理念主要在于防止股份购买者开展“诉讼投机”。而日本并不没有要求原告在其所诉的不正当行为发生时即为股东,《日本商法典》第267条第1项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必须是自6个月以前持续拥有股份的股东。,提出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建议规定。其第44条建议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应当在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发生时持有并持续持有公司股份(另一种意见是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发生前6个月持续持有公司股份)。实际上,前述第一种意见采用了“当时拥有原则”;第二种意见则仿效日本做法,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做法。
笔者认为,我国正处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初建阶段,在规定原告股东资格时应该持相对宽容态度。《征求意见稿》在建议规定“当时拥有原则”时,完全没有除外规定是不妥的。那些在侵害行为发生后才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在受让股份时可能并不知道侵害行为的存在,而这些侵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后果,却可能一直延续直接或间接损害到此后受让股份的股东的利益。如果采用“当时拥有原则”,就可能会损害这些股东的民事权益与诉讼权利⑶。笔者认为若采用该原则应允许例外:(1)法人股东终止、自然人股东死亡,其(概括)继承人可享有诉权;(2)受让公司股份时,不应当也不可能知道侵害公司行为的股东可享有诉权;(3)若对公司的侵害行为或后果仍在继续进行或持续对公司产生影响时,新股东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权;(4)原告股东的资格丧失是因公司控制者的不当行为所致时,原告股东仍可继续享有诉权。
至于对原告股东持股时间的限制中是否要规定确切的持股期限,日本和我国台湾各自规定了不同的持股时间(日本为6个月,台湾为1年以上)。日本法律设定该要件之目的是为了防止滥诉,但对其真正的实际效果,许多学者颇感疑问。因为真想要滥用诉讼的股东完全可以在取得股份后等上6个月再提起代表诉讼⑷。故笔者认为此规定中国立法不易采纳,况且在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购买股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股市的买卖差价中获利,所以他们持有的期间通常不会太长。如对原告资格规定过长的持股期限,实际上将把大部分股东排斥在原告范围之外,显然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要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尤其是社会投资者的目的不符。⑸
(二)股东持股数量的限制
美日立法均承认股东持股数量之多寡对于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资格不发生影响。因为从股东平等原则出发,即使股东只拥有一股,但只要符合其他条件,。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14条则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必须是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10%以上的股东。这是由于美日立法将代表诉讼提起权视为单独股东权,而台湾立法视其为少数股东权。代表诉讼提起权究竟是单独股东权,还是少数股东权?有学者认为,其纯为各国立法者的政策选择⑹。两种选择均有优劣之处,若将其视为少数股东权,无疑限制了股东行使此权利,但有利于防止个别居心叵测的股东滥用权利;而若将其视为单独股东权,则可鼓励中小股东监督公司正常运营、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但其他配套法律机制失位时,也会导致个别股东出于不良目的而滥用诉权。
最高院《征求意见稿》对股东持股数量也进行了建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应不少于10%,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应不少于1%。笔者认为该规定不符合我国实际,理由如下:(1)我国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有上限限制,不可能有不特定的多数公众参加,尤其是在公司股东数量很少的情况下,每个股东的权利均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即便其持股比例很低。否则这些小股东在公司受到高管人员或大股东侵害时,既不能提起代表诉讼,又难以转让其股权(对此种情形下的公司股权恐怕也无人敢受让),其正当权益便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且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之性质,各股东在公司成立或新股东加入时,彼此是有选择权的,以受让方式滥用代表诉讼的情况极少可能在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即便发生,其他股东也完全可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式加以阻止。故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应不少于10%”实无必要。(2)只有使大多数投资者能够自然而然具备原告资格,才能使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真正起到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目的。因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应不少于1%”的建议标准过高。若按此规定,我国绝大多数投资者恐怕都不具备原告资格。以联通公司为例,根据该公司2003年6月30日披露的信息,其总股本为196亿多,第二至第十大股东均是流通股股东,均为各证券投资基金。其中第二大股东持股8000多万,也仅占总股本的0.44%。据此可知,该公司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数额均达不到原告资格条件要求。⑺
笔者同时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是股东权所涵盖的当然内容,若依股东所持股额而区别对待,剥夺一定数额标准下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有悖于诉权平等和股东平等原则。何况用股额限制以防止滥诉亦非良策,因为高于该标准者未必不是滥诉者,低于该标准者未必就是滥诉者⑻。故我国在导入代表诉讼制度时,应采单独股东权,不必以持股数额的多少来确定股东诉权的有无。至于股东有可能滥诉的问题,可通过完善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费用担保等配套机制予以解决。
(三)原告股东公正善意原则
鉴于股东代表诉讼时常被滥用作为谋求股东私利的手段的现实,又鉴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结果对其他股东和公司产生既判力,很多国家立法上均要求起诉股东是真实的、慎重的和善意的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美国《模范公司法》第7.41条第2项要求,原告股东在落实公司的权利时,能够公正、充分地代表公司利益。《联邦民事诉讼条例》第23条第1项也规定:“若原告在行使公司或社团的权利时,不能公正、充分地代表与之处于相似地位的众股东或众成员的利益,则不得维持代表诉讼”。而《日本商法典》对于原告股东代表其他股东之公正性及充分性未设明文规定,我国最高院《征求意见稿》也未提及原告股东的公正善意原则。但笔者认为我国采用此原则实属必要,至于原告股东能否做到这一点,可授权法官秉持公正理念,斟酌个案情形而裁定。但如下情形中,法官决不能裁定原告股东坚持了公正善意原则:(1)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是为了谋取其所在公司的竞争对手的利益,或是为了谋取与自己持股比例不成正比的私利;(2)原告股东曾参加、批准或默许所诉不正当行为。这其实是仿效美国立法上的“净手原则”,即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是那些没有支持、批准或者追认公司董事会等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成员。(3)原告股东以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
三、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从前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概念中,我们可知股东欲提起代表诉讼必须是在公司怠于行使诉权的前提下,换言之,股东具备了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并不等于股东在公司遭受不正当行为损害时可迳行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其还应首先征求公司的意见,即公司是否对该侵害行为提起诉讼。对此,美国主要采用“竭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即原告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前,必须首先请求董事会采取必要措施行使公司的诉权请求,只有当公司明确拒绝股东请求或者对股东请求置之不理时,。该原则的主要作用在于,可向公司提供由公司亲自出面提起诉讼的机会,因为公司毕竟是真正原告。若在股东的请求下,公司机关能公正、合理的解决问题或不法行为人如董事、监事、经理等纠正其错误,也就无必要浪费人力、物力再提起代表诉讼了。
最高院《征求意见稿》第45条建议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原告股东“已于2个月前请求公司提起诉讼,但公司未起诉的”。实际上,这就是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但公司机关通常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原告股东到底向哪个机关提出请求最为妥当呢,《征求意见稿》未作规定。笔者认为:(1)设有监事会的公司中,股东应首先向监事会提出申请。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具有监督权,监事会是公司法定监督机构,而我们所要构建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就是股东行使监督权的一种诉讼制度,故股东提请其决定是否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便理所当然了。因此,我国公司法应当加强监事会职能的立法完善,增加规定监事会对于原告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审查职能。(2)公司未设立监事会或者原告股东证明监事会已丧失公正、独立性时,原告股东可向董事会提起请求。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仅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但提高其地位,扩大其权利,确立其核心地位,应是我国公司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故董事会对致害人违法、不适行为之监督应是其职权内的事情;⑼(3)若董事会、监事会都丧失公正性时,原告股东可向股东会提出请求,因为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自然有权决定股东提出的代表诉讼请求。当然,前置程序的规定也非绝对,若控股股东或控制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管人员是侵权人或与侵权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公司机关已无法真实表达公司自己的意思,在此情况下,。
原告股东向有关公司机关提出请求后,须等待多长时间才可提起代表诉讼呢?美国《模范商事法》第7.42条明确规定:“除非股东被提前通知请求被拒绝,或者股东自其请求之日起等待90天会给公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股东必须自其请求之日起等待90天届满为止。”《日本商法典》第267条也规定:“自6个月以前持续持有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公司自前项请求之日起30天以内,不提起诉讼时,前项股东可以代为公司提起诉讼。因经过前项期间,使公司有不能恢复损害之虞时,虽然有前项的规定,但第一项的股东可以立即提起前项诉讼。”我国台湾《公司法》在时间上仿效了日本的做法(也规定为30日),不同之处是没有考虑例外情况。结合上述立法例,笔者认为:(1)从缩短股东代表诉讼的诉前准备时间,降低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最高院《征求意见稿》建议规定的2个月期限可供我国立法参考;(2)我国立法应借鉴日本的例外规定,股东自其向公司机关提出请求之日起等待法定期限届满有给公司造成不可恢复损失之虞时,可迳行提起代表诉讼,如《征求意见稿》第45条规定的相关情形(有关财产即将被转移、有关权利的行使期间或者诉讼时效即将超过的)发生时。
四、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担保
诉讼费用担保制度,指在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以便在原告败诉时,被告能从原告所提供担保的金额中获得诉讼费用补偿的制度⑽。该制度是对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一种制约机制,旨在限制居心不良的小股东和律师无理缠讼,为谋取一己之利而坑害公司利益。从效果上看,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遏制了无理缠讼的恶性膨胀,但同时也加重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负担:;(2)提供诉讼费用担保的原告股东在败诉后,既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用,又要承担被告的诉讼费用。因此,。诉讼费用担保制度最早始于1944年美国纽约州对其《普通公司法》的修改,此后美国许多州和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设立该制度。但美国1982年以来的《模范商事公司法》却删除了关于诉讼费用担保的条款。现今取消股东代表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已成为美国现代商事立法的潮流。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也应暂缓导入诉讼担保制度。这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我国传统厌诉观念的消极影响尚存,现在应鼓励公民对诉讼程序资源的充分利用而非抑制⑾。何况我国现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尚未被立法明文规定,此类案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如何激活股东代表诉讼机制。当然,如果我国将来大量出现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且股东滥诉现象较为严重,其他配套措施也效果不佳时,也可考虑导入该制度。最高院《征求意见稿》第47条也对此制度加以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恶意诉讼情形,,,担保数额应当相当于被告参加诉讼可能发生的合理费用”。此规定从操作层面上看显得过于笼统,笔者认为要求原告提供担保应符合相关要件:,至于申请时间,;(2)被告要证明原告起诉是出于恶意,举证责任在被告;(3)担保范围应包括诉讼费用及由于原告恶意诉讼而给公司和被告造成的损失,至于担保的具体形式,现金、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均可;,。至于担保数额,,立法上应设一最高限额,。
五、原告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一)胜诉时原告股东的权利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原告胜诉时,被告应承担案件的受理费用和其他法定费用,但原告仍应承担律师费及其他不由被告人承担的费用。但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由于大多数原告属于个人股东,往往无力承担高额的律师费及其它费用,而且,即使原告股东耗费大量资金最终胜诉时,其直接受益人为公司,原告股东因此得到的股份增值是很少的。这一问题若不能获得解决,势必会打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积极性。在美国,作为一般原则,当代表诉讼获胜、给公司带来利益时,原告股东有权从公司获得一笔合理费用的补偿。日本于1993年修订《日本商法典》时也作了类似之规定。笔者认为,公司既享受了利益就应当负担因该利益所付出的代价,这是理所当然的,故我国立法上亦应赋予胜诉原告股东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即在代表诉讼获胜时,原告股东除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从败诉的被告手中获得法定诉讼费用的补偿外,有权请求公司支付律师费及其他必要费用,从而补偿原告股东为获得胜诉判决而支付的财产利益。但公司仅在其因胜诉所获取利益范围之内支付该费用,如果原告股东的实际诉讼费用高于公司所获取的赔偿,公司也仅在其受偿数额内对原告股东进行补偿。⑿
另外,美国立法上还规定胜诉原告股东具有“比例性个别赔偿请求权”。在一般情况下,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就足以维护原告股东作为诉讼原告及公司股东双重身份所应拥有的利益,但在侵害公司利益的主体是公司股东尤其是公司大股东时,被告大股东又与原告股东一起就由其对公司的赔偿金所恢复的公司利益进行分配,这样,无论其不正当行为是否得到纠正,被告大股东均是最大的受益者而无丝毫损失,这无疑有失公平⒀。因此,为充分发挥法律的补偿和教育功能,保护诚实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积极性,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立法经验,,当然这必须在不害及公司债权人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
(二)原告股东的告知义务
,有义务立即向公司告知该诉讼。《日本商法典》第269条就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之后,必须将起诉一事告诉公司。公司及原告以外的其他股东可以在代表诉讼开始后以共同诉讼人身份参加诉讼。其立法宗旨在于:代表诉讼实包含有为全体股东及公司之利益提起诉讼之本质,如果其他股东因为有人已先行提起诉讼以致没有对同一董事提起代表诉讼,嗣后如果该起诉股东私下和被告董事达成和解而撤诉,则其他股东将无所适从⒁。美国立法由于将公司列为名义上的被告参加代表诉讼,而没有设置原告诉讼告知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导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时,应视公司在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⒂决定是否设置原告诉讼告知义务。若采用美国做法,将公司视为名义上的被告,则无设置原告诉讼告知义务之必要;若将公司视为共同诉讼人,则应设置原告诉讼告知义务,若原告股东怠于履行此义务而使公司利益受损,须负赔偿责任。
(三)败诉时原告股东的责任
对败诉股东的责任,《日本商法典》第268条之2项规定:“股东在败诉的情形下,如果没有恶意,公司不负担损害赔偿责任。”依相反解释,败诉股东若对代表诉讼之提起存在恶意,则应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⒃。笔者认为此规定可为我国立法借鉴,即败诉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必须以主观存在“恶意”为要件。所谓“恶意”,应理解为明知有损于公司利益而仍代表公司提起不适当的诉讼。对于不存在主观恶意的股东,即使败诉也可不对公司承担任何责任。这样可鼓励广大善良股东积极参与公司经营的监督,维护公司利益;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诉讼,避免公司利益不必要的损害,应健全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等配套机制。
我国台湾《公司法》还规定了败诉股东对被告的责任,其第215条规定:“提起前条第2项起诉所依据之事实,显属虚构,经终局判决确定时,提起此项诉讼之股东,对于被诉之董事因此诉讼所受之损害,负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其为防御诉讼所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若能由公司获得补偿,则我国立法中无设定此种责任之必要。
注:
⑴ 段厚省.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地位 [J].法学杂志.1998(5)。
⑵⑹⑽⒃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24,515,347,355。
⑶⑸⑺ 王欣新.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J].经济法、劳动法学.2004(4)。
⑷ 周剑龙.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A].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68。
⑻ 江伟 段厚省.论股东诉权[J].浙江社会科学,1999(3)。
⑼ 张民安.派生诉讼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6)。
⑾ 杨静.股东派生诉讼当事人之探讨[J].经济师,2004(3)。
⑿ 周友苏.公司法通论[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598。
⒀ 孙英.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⒁ 宫晓艳.股东代表诉讼之主体[J].法治论丛,2003(5)。
⒂ 公司在代表诉讼中法律地位,各国立法颇不一致,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
最新资讯
-
08-07 1
-
08-06 2
-
08-08 2
-
08-13 0
-
08-21 0
-
08-17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