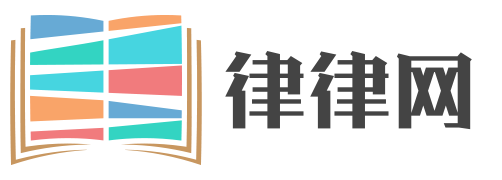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
发布时间:2019-08-14 17:21:15
一、对现行制度的反思并提出核心问题
在现行公司法中,对于股东之间争议的解决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可以找出的原则性支点是《公司法》第20条及183条。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利……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183条进一步指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它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下面,我们以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作为反思的出发点:在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中,大股东持股百分之六十,两个小股东各自持股百分之二十。为了表示大股东善待小股东的诚意,三人在公司章程中相约:股东会在作决议时,一人一票,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大股东歧视小股东的威胁彻底解除之后,小股东精诚团结歧视大股东的可能性又诞生了。在两个小股东的协作下,公司连续通过一系列有损大股东利益的决议。公司章程中一人一票的约定给小股东提供了合同依据去实现这个结果。而且根据《公司法》第43条保护“公司自治”的精神,这个决议的有效性在法律上亦无障碍。
在这个案例中,大股东其实是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虽然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他原则上仍然有查账权和质询权这种边缘化权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无法避免在拥有公司大部分资产的前提下,却要被动地接受小股东联盟通过合法程序做出的所有决定。在当初订立公司章程的时候,大股东也只是想表示自己的合作诚意。很明显,他对小股东联盟的力量和可以造成的结果没有足够的估计,这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至关重要的是这种状态直接导致公司存在的基础,即他们三人一起经营合作所依赖的信任慢慢地消失。实质上这是有失公平的,也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大股东可以通过183条提供的渠道来申请公司解散,以退出公司。但是,183条是个解散公司之诉,这违背了鼓励经济发展的立法原则。我们需要注意,本案中,大股东可能希望解散公司得以全身而退。但是,两个小股东却可能还有很高的积极性去保护公司在市场上已经形成的良好信誉、提升公司的业绩,为我们的社会创造财富。183条在根本上消灭了小股东的这种期待,它牺牲了一部分股东的利益以施惠给另一部分,在实体上造成了不公平。综上所述,183条在股东争议案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将是很有限的。法律应该给大股东提供一个退出公司的途径,同时也给小股东联盟一个机会来继续公司的运营和发展。这种情况下,小股东联盟实现他们决议的前提就是他们要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大股东的股票。
前文最后提出的这种进路可以使股东之间的关系达到实质性平衡,并保持公司良好的经济前途。宏观上说,对于引入这种进路,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在现行公司法所构建的体制中,以上这种进路还缺乏法律依据,这是在法律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不可否认的是“意思自治”和减少法律对公司内部事物的干预是当代公司法的特征之一。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公司自治”原则和法律干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形态和法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一样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二、我国股东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法技术层面
(一)大陆法系对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关系的认识——基本态度、渊源及功能
虽然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承认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形式上的诸多不同,但是,在原则上又认识到了这两种法律形式内部机制的相似之处。正如卡尔拉伦茨教授在其书中所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仅仅在与作为团体的公司关系上,而且在股东的相互关系上,须履行合伙法上的诚实信用义务。[1]对这种诚实信用义务的存在基础,他也做出了解释:依据德国法,合伙企业本身并没有“团体章程”,从类型上看,这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一些人的联合,因而,每个合伙人对联合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一般是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经营管理,经营的成功或者失败就主要取决于各个合伙人的才干信用,也取决于全体合伙人的和睦相处。[2]很明显,在德国法体系中,也承认合伙企业和小型有限责任公司在股东内部关系上的相似之处,把股东或者合伙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和睦关系作为这类经济体存在的重要基础。这种思路与Hoffmann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不公平歧视”条款进行解释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相似的,甚至是同源的。在法律渊源的问题上,Hoffmann法官在O Neil v Phillips案中,特别强调了英国有限责任公司与“罗马式合伙企业”(Roman Societas)[3]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正是他启动衡平法救济的依据。因为,英国衡平法是深受罗马法及教会法(Canon)影响的,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核心思想。[4]另一方面,罗马法对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对社团性质认识的影响深远程度自不待言。
以上的比较表明德国法和英国法对有限责任公司争议解决机制的态度是趋于一致的,而且其背后依据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渊源也有着诸多的交叉点。依据比较法中的“功能主义原理”[5],,但是,它们都具有保护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功能,也完成了保护股东之间关系在实质上公平和正义的任务。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宏观的司法态度、法学渊源和功能性分析上看,在大陆法系体系中,尤其是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我国,引入英国公司法的“不公平歧视”条款是可能的,而且具备相当理论基础。
(二)以“正当期待”为切入点
宏观上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引入英国公司法中进路的理论支持,而在微观上找准引入此进路的切入点,才能使它契合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体系,达到改善股东争议解决机制的目的。在现行体制下,当股东之间原始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一部分股东通过公司章程约定的合法程序所吸收的时候,法律不能够及时介入保护股东的期待和他们的共识,或者为股东提供一个公平的退出机会,这就造成了我国公司法与德国和英国公司法相比,有功能上的缺失。以这种思路为指导,我们可以试验性的引入英国公司法中的“正当期待”概念来填补这个空白。
本质上说,“正当期待”主要体现的是股东在进入公司时对其依附于财产权上的管理权的一种认识,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意思表示。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往往是他们不论出资比例的大小都享有持续的、积极的参与公司事务管理的权利。在我国,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采纳工商部门提供的公司章程的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股东之间的一些意思表示没有被直接写入公司章程中去,这为股东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留下了隐患。依据大陆法系对意思表示客观价值的认识,对意思表示作出解释应该查明真正的意思,不应拘泥于词句的字面意思。并且,解释合同应依诚实信用并注重交易习俗之要求为之。[6]这种理论可以说与Hoffmann法官在459条下,对“不公平歧视”的解释和“正当期待”概念的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精髓都在于探询意思表示的实质内容,制止对合同权利的滥用,以达到保护善良、健康商业习惯的目的。但是,我们有必要认清一点,普通合同法中的原则及具体条款主要是针对有较强债权性质的合同的,这种原则有时候又不足以规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关系。
基于以上的论证,在公司法体系中发展独特的制度来解释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十分必要的。“正当期待”原则,如前文所述,在特定条件下扩大化地解释了股东的权利,并试图认清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哪些权利是股东在公司这个经济体中应该持续享受的,并且不能被公司章程中约定的合法程序所吸收。这种进路恰恰可以与《公司法》第20条契合,它充实了股东权利的内涵。这样,那些依照公司章程行使,但在实体上造成不公平结果、违背了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它股东利益”了。
至此,在法技术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现行《公司法》的确还在股东争议解决机制上存在着功能性缺失。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的论证,已经初步证明了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中引入“合法期待”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这种引入并不等于照搬。社会学及法文化学说,法技术以外的因素,也对法学的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改良——社会形态及法文化层面
英国公司法中的进路如果想要在我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必须依照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做出改良。首先,从社会形态上看,英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法制社会阶段,法律和社会关系之问的互动可谓无处不在。而且,市场经济模式在英国已经十分成熟,其内部自我调节、自我规范的商业道德体系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相当的约束力,正如Cheffins教授所说,信誉资产(reputational asset)对一个职业商人来说和经济上的资产一样重要。[7]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公司自治”在英国有着十分坚实而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公司法还是会适当的介入来保护股东的权利和实质上的正义。相比而言,成熟的法制社会在我国尚未形成,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社会形态也正经历着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在这种条件下,虽然鼓励“公司自治”观念可以促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但是,要认识到我们还缺乏从根本上接受这个制度的广泛社会文化基础。经济转型时期的市场自律规范、行业标准都尚不完善,可以说非法律性的“自治规则”还并不能有效的约束市场参与者的商事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强调的是“公司自治”,而不是要创造一个规则的真空来放任公司及内部股东的行为,如果公司本身不具备“自治”能力的话,司法还是需要介入和干涉的。在一个发展并不完善的市场中,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实际的公平正义必须通过司法手段树立起来。综上所述,我们还不具备在司法上严守“公司自治”原则的社会条件,也还不能大幅度地减弱法庭对公司内部事务的干预。也就是说,依据我国的社会情况,法律规范的涉及范围、法庭对股东之间协议的解释、填补漏洞的力度还应强于英国公司法的标准。
其次,与英国的法律文化所不同的是,中国对“法”本身的传统理解是“惩罚的措施”而非“维护权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基本上认为被卷入到法律诉讼中对自己及家人的名誉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即使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30年的今天,“和气生财”依然是生意场上的主流文化,这就体现了中国社会中特有的“厌诉”情节。所以,前文提及的英国法庭所预防的“诉讼权滥用”(floodgate litigation)和“机会主义诉讼”的现象不太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司法环境中。基于这种法文化的差异,较英国公司法对股东争议采取比较谨慎严格的方式,我国的立法应该尽量放宽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鼓励利益被歧视的股东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争议解决机制可以有保留地参照英国公司法的进路,引入“正当期待”这一概念。在公司的存续基础为股东之间相互信任,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是股东在进入公司时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一旦股东被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程序排除在公司管理之外,他可以依据“正当期待”原则,提起诉讼,退出公司。依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及法文化状况,较英国法不同的是,在提倡股东进行自力救济,保护“公司自治”的同时,也应该鼓励股东依法提起诉讼。虽然市场本身有自愈能力,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不规范的市场体制所提供的自愈途径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不公平的。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以诉讼手段申请退出公司的股东,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多少是真正愿意退出公司的,他们退出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法的权利受到了损害。通过自力救济的途径,他们急于退出公司的心理很可能被利用,股票价格很可能被低估。更糟糕的情况是,大股东完全可能利用自己对公司财产的控制权故意抽逃财产,以达到贱收退股股东股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并强制占据主导地位的股东以此价格购买股票。
在W.Ong与C.Baxter教授关于中英公司法比较的文章中提到“对中国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研究”,[8]反之亦然。在英国最近的公司法修改草案中(Company Law Reform Bill),把小公司的问题放在首位解决(think small first)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因为通过数据调查,英国的注册公司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有限责任公司,而上市公司的数量还不到注册公司总数的百分之一。[9]可见,在相对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小公司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如何解决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的股东纠纷也将成为我国公司法中的重要议题。而本文为这个议题提供了一种比较法视野中的解决方案。
注释:
作者简介:周天舒(1981—),男,汉族,北京市人,英国伦敦大学法学硕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
*英国爱丁堡大学
[1](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华、徐国建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2]见前引,第185—186页。
[3]See Supra note 10 Pp.280。
[4](德)K 茨威格尔 H 克茨:《比较法总论》,贺卫方、米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5]见前引,第48—49页。
[6](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版,第400页。
[7]See Supra note21 Pp.97。
[8]Kingsley T.W.Ong and Colin R.Baxter,“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 Element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mpany Law”(1999)48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pp.120。
[9]See Supra note 18 Pp.234。
最新资讯
-
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具有股东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
08-08 0
-
08-24 0
-
08-03 0
-
09-01 0
-
08-27 1
-
08-09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