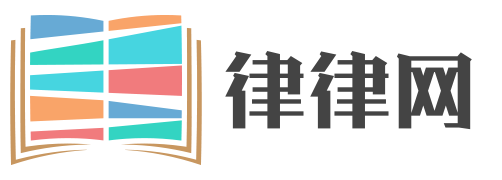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之探析
发布时间:2020-03-30 00:12:15
【关键词】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扩展趋势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事项因其与一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故而使得目前存在的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尚未就此作出统一规定,而是主要由各国有关仲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分别加以确定。[1]根据各国有关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国际商事争议的仲裁范围仅限于一定特性的争议,[2]而诸如证券交易、反托拉斯、知识产权等均属于传统的不可仲裁事项,被排除在可仲裁范围之外。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加大,国际商事争议愈益增多,为了迅速解决此等争议,促进国际经济的良性发展,于是各国对仲裁所实施的政策逐渐放宽,各国对仲裁支持的力度亦在加大,再者晚近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可仲裁性问题与公共政策概念相脱离,[3]因而国际商事争议的可仲裁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原先许多属传统的不可仲裁的事项已经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或者正在向可仲裁的方向演进。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并且结合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就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略加述评。
一、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立法趋势
一般来说,各国仲裁立法大都将可仲裁的争议事项限于商事争议事项,故非商事争议事项属于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4]而且,在可仲裁的商事争议事项方面,起初一些国家的法律对其范围规定的也比较狭窄,即涉及证券交易、反托拉斯、知识产权、破产争议等事项,长期以来一直被排除在仲裁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外。[5]然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即各国国内立法的趋势是减少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限制,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范围持较为宽泛的的态度,亦即上述原本属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向可仲裁争议事项转化,而且对于商业活动所产生的争议,只要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就决不轻易地援用“争议事项不具备可仲裁性”这一保留条款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
(一)关于证券交易争议问题
证券交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证券交易所与其成员之间、各证券交易机构之间、经纪人与客户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因经纪人与客户之间的交易而产生的争议。[6]对此证券交易争议,美国国会于1933年颁布的《联邦证券法》规定,对于涉及该法适用所产生的所有争议,。可见该法将证券交易争议排除在可仲裁范围之外。美国国会于1934年制定的《联邦证券交易法》与《联邦证券法》持相同立场,,从而排除了仲裁解决。此种立法之理由是考虑到证券投资者和证券经纪人谈判能力的差异,,而且因着眼于稳固整个美国证券市场以及保护投资者的需要,故禁止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放弃司法诉讼权利。不过,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即1925年通过的《联邦仲裁法》规定,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是有效的、不可撤销的、可执行的,除非有符合法律或争议的与撤销所有合同一样的理由”,[7]从而确定了证券交易的可仲裁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美国欲结束长期以来司法对仲裁的敌对态度,联邦支持仲裁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实质上是主观可仲裁性对客观可仲裁性的发展提出要求的外部表现。针对上述并行而又相矛盾的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问题,美国并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从证券交易争议不可仲裁到国际证券交易请求权可仲裁而国内证券交易请求权不可仲裁再到国际、国内证券交易请求权均可仲裁。这代表了证券交易争议的可仲裁性的立法趋势。
(二)关于反托拉斯争议问题
反托拉斯争议能否仲裁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可仲裁到可仲裁的发展过程。反托拉斯问题不能提交仲裁曾是一条固定的规则,,否认其可仲裁性。[8]但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放宽了对反托拉斯争议问题可仲裁性的限制。例如,过去德国法不允许将反托拉斯争议交付仲裁,但按照德国1974年《限制贸易实施法》第91节的规定,,在德国将有关反托拉斯的现有争议交付仲裁是可能的;德国的反托拉斯法第91条、第98条第2款规定所有已经发生的、某些将来发生的反托拉斯争议,对德国市场不产生影响的出口卡特尔争议以及其他对德国市场不产生影响的反托拉斯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89年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77条规定,反托拉斯等国际性质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其也作了一定的限制。[9]例如,在德国,当事人若将未来的反托拉斯争议提交仲裁,。美国在此问题上,仍然是通过其判例来确定在反托拉斯争议问题可仲裁性的发展趋势的。
(三)关于知识产权争议问题
在知识产权争议可否仲裁的问题上,因其不同类型而有所差异。各国实践表明,版权和专有技术争议一般都是可以仲裁的。[10] 对于专利和商标权方面的争议之一即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和许可协议项下的使用费争议,各国法律一般也允许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1] 例如,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除了专利和商标权的有效性问题之外,一般的知识产权争议皆可以交付仲裁。[12] 美国在1982年以前,侵犯专利权的争议尚不能通过仲裁这种“私了”的方式解决。[13] 但是美国国会于1982年在《美国法典》的第35章加入了第294节,明确规定专利争议可以进行仲裁。[14] 同年,美国还颁布了《半导体芯片保护法》,,除非首先通过自愿谈判、调解或有拘束力的仲裁解决。[15] 对于专利和商标权方面的争议之二即专利和商标权的有效性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争议,长期被绝大多数国家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16] 例如,美国一向认为由于对无效专利进行制裁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因此专利是否有效就不宜适用仲裁程序,。在法国,仲裁员无权宣布专利或商标无效。在荷兰,专利的有效性问题不具有可仲裁性,。在意大利,专利、商标是否有效,也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然而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各国逐渐放松了对专利的有效性和强制许可争议可仲裁性方面的限制,允许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例如,美国《联邦专利法》1983年和1984年修正案即允许当事人约定将任何有关专利效力或侵犯专利权的未来或现有争议,以及任何涉及专利权实施受到阻碍的未来或现实争议提交仲裁。但是该法同时规定,有关专利效力和侵犯专利权案件的仲裁裁决仅在仲裁的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对其他任何人没有约束力或效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修正案允许当事人约定:如果专利在仲裁裁决中被认定有效,,;但是,此种修改从修改之日起支配当事人的权利,并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利用,。美国专利法上述修正案的规定无疑体现了立法者在鼓励仲裁解决纠纷与保护第三人及公众利益两种政策之间的平衡。[17] 再如,瑞士专利商标局于1975年11月15日发表声明,仲裁庭作出的关于专利、商标的效力的裁决,可以做出撤销登记的依据。[18]
此外,各国立法在破产争议、消费者争议、劳动争议等方面也呈现出从不可仲裁向可仲裁方向的发展。
二、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司法实践态势
(一)关于证券交易争议问题
前已述及,美国《联邦仲裁法》与《联邦证券法》、《联邦证券交易法》在证券交易争议可否仲裁的问题上彼此存在着冲突,对于此种冲突的解决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起初,,对证券交易争议持不可仲裁的态度,例如, v. Swan)一案中,[19]确立了“基于1933年《联邦证券法》所提起的申诉是不可仲裁”的原则。但是, Sherk v. Al2berto - Culver Co. )案[20]中,遭到了否定。,即它区别国际证券交易争议和国内证券交易争议,确认在国际领域,美国《联邦仲裁法》比1933年《联邦证券法》和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优先予以适用,但该案还未能推翻Wilko v Swan一案中所涉及的国内证券交易请求权的不可仲裁性。1987年, Shearson / American Express Inc. v Euqene McMahon)案[21]中,又一次重申了证券争议的可仲裁性原则,而且是开始承认国内证券争议也可提交仲裁,尽管并未直接推翻Wilko v. Swan案所确立的原则。直到1989年, v. Shearson / American Express案[22]中最终推翻了Wilko v Swan案所确立的原则,进而确立了仲裁庭对证券交易的管辖权。,对美国《联邦仲裁法》与1933年《联邦证券法》应作一致的解释,根据《联邦证券法》第12节第2款,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订立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应予支持。至此,除了某些例外,无论是国际证券交易争议还是国内证券交易争议,都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
(二)关于反托拉斯争议问题
关于反托拉斯争议,,并且成为一个牢固确立的原则。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 P. Maguire &Co.[23]案中的判词反映了这一立场。在该案中,,从而确立了“美国安全”规则。[24] 然而, Motors Co.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案[25]中发生了逆转,首次确认反托拉斯争议是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事项。在该案中,,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 P. Maguire &Co. 案中提出的否定反托拉斯争议可仲裁性的四项理由。[26] 此后, Caribe Inc. vNokia-Mobria Inc. and Cellular World Inc. )案[27]中,将三菱汽车公司案的原则适用于纯国内交易中的反托拉斯争议。此外, ;。
(三)关于知识产权争议问题
关于专利侵权之诉,。但随着1982年美国国会在《美国法典》中规定专利争议可以进行仲裁后,与此法相适应,在以Rhone - Pollens Specialifies Chiniques v SCM Corp.[28]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判例中,。。[29] 至于专利和商标权有效性的认定问题, Corp. v. Millard[30] 以及Tire rubber Co. v. Jefferson Chem. Co.[31]等一系列案件中,认为此方面的争议不宜由仲裁解决。但1983年的美国《联邦专利法》和1984年的修正案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专利和商标权有效性的认定问题具有可仲裁性,。关于版权争议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与专利、商标争议等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并未就此作出立法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32] 例如,在Kamikaze music Corp. v.Robbins music Corp. 案中,;在Saturday Evening Co. v. Rumble seat Press Inc. 案中,。
此外,各国司法实践在破产争议、消费者争议、劳动争议等方面均确认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
三、我国的有关规定及其评析
在我国,关于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仲裁法》作了原则性规定。该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⑴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 ⑵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可见,《仲裁法》在仲裁范围方面的立法例采用的是结合式,[33]即立法上兼采概括式和列举式两种方式来界定仲裁范围,这既反映了逐渐拓宽仲裁范围的态势,又避免了概括式的模糊,是立法技术上的进步。从仲裁范围的确定标准来看,大致包括: ⑴仲裁主体的平等性,即当事人的地位应当平等,亦即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如行政争议即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只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才能仲裁; ⑵仲裁事项的可处分性,即仲裁事项必须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民事实体权利,亦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随意行使、主张、变更或者放弃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因此,凡当事人无权自由处分的事项如《仲裁法》第3条第1款列举的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因涉及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身份关系而不能以仲裁的方式解决; ⑶争议内容的财产性,即可以提交仲裁的纠纷须为民事经济纠纷,主要是合同纠纷,也包括一些非合同的财产权益纠纷,因此,凡不具备财产性的身份权纠纷或虽涉及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但建立在身份关系基础上的民事纠纷均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据此,在我国下述争议可以仲裁:[34] ⑴合同纠纷。具体包括: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等合同纠纷;技术合同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商标合同使用纠纷;房地产合同纠纷;涉外经济贸易合同纠纷;海事、海商合同纠纷。⑵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主要指侵权纠纷,包括:海事侵权纠纷;房地产侵权纠纷;因产品质量引发的侵权纠纷;涉及工业产权的专利、商标侵权纠纷;涉及著作权的侵权纠纷。
此外,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9条规定:“与股票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按照协议的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第80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场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应当签订证券争议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证券经营机构之间以及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交易场所之间因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引起的争议必须采取仲裁方式解决。上述机构签订的与股票发行或者交易有关的合同,应当包括证券争议仲裁条款。”可见,在我国与股票的发行或者交易的有关争议,也可提交仲裁解决。另外,;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通知》规定,我国在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声明表明,我国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显然,根据此规定其仲裁范围也较为宽泛。
所以,我国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限制较少,也即可仲裁事项的范围较为宽泛,与国际社会在争议事项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上相接近。
但是,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却与此不相衔接,存在矛盾之处。例如,:对专利申请有异议的,由专利局作出审议;第60条规定:对专利侵权行为,专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专利管理机关处理,。: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由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第39条及其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2条规定: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进行监督检查;第29条规定:当事人对监督检查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从上述规定可见,有关专利侵权、商标侵权、竞争法方面的争议不能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而根据其他法律法规这些争议却可以通过仲裁方式加以解决。[35] 因为,我国《仲裁法》第65条规定,涉外仲裁制度“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这一概括性的范围足够包含知识产权争议。另从我国加入《纽约公约》的声明看,不仅合同纠纷、侵权及所有权争议都可交付仲裁。照此声明,知识产权合同争议、侵犯知识产权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在我国均属可仲裁之列。事实上,CIETAC已把包括知识产权转让在内的涉外经济贸易争议纳入受案范围,并受理过若干案件,其所作裁决尚未见报导因此而被撤销或被拒绝执行。与知识产权争议可以仲裁的理由相似,竞争法方面的争议特别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及其赔偿不能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而且这也与我国较宽泛的可仲裁范围不相一致。显然,对此应从立法技术与内容上加以修改、完善,使上述有关法律法规相互衔接,同时体现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诚意,并且与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以及我国较宽泛的可仲裁范围相一致。
【作者简介】
黄进,武汉大学教授;
马德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参见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2]参见刘晓红、许旭:《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在欧美的发展趋势》,载《2005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论文集》。
[3]参见前注[2],刘晓红等文。
[4]参见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32页;赵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91页;马德才:《论国际商事仲裁中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参见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7、348-349页。
[6]参见前注[1],赵秀文书,第74页。
[7]9U. S. C. 2 (1994).
[8]See Karl-HeinzBǒckstiegel ,op. cit. , at 194. 转引自赵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9]参见赵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0]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78-179页。
[11]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77页。
[12]参见钟丽:《知识产权争议可仲裁性问题比较研究》,载《2005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论文集》。
[13]See Kevin R. Casey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PatentLaw, 3. Fed. CircuitB. J. I ,5 (1993). 转引自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4]参见前注[1],赵秀文书,第78-79页。
[15]参见前注[1],赵秀文书,第79页。
[16]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77-178页。
[17]参见前注[2],刘晓红等文。
[18]参见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19]赵秀文主编:《国际商事仲裁案例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6-104页。
[20]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74-75页; 417 V. S. 506 (1974) , reported in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 1976) , pp.203-204.
[21]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81-182页; 107 Supreme Court Reporter (1987) 2332, reported in Yearbook CommercialArbi2tration XIII(1988) , pp. 165-176.
[22]参见前注[1],赵秀文书,第75页;前注[9],赵健书,第182页。
[23]391F. 2d 821, 827-28 (2d Cir. 1968).
[24]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72页。
[25]473 V. S. 614 (1985),reported in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XIII (1988) , pp. 555-566.
[26]前注[9],赵健书,第173-174页。
[27]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ume XV I (1991),pp. 635-640.
[28]684F. 2d 228 (2d Cir. 1982).
[29]参见[美]大卫·普朗特:《美国的知识产权争议仲裁问题研究》,江波译,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6年第5期。
[30]531F. 2d 585 (D. C. Cir 1976).
[31]182 U. S. P. Q. 70 (2d Cir. 1974).
[32]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78-179页。
[33]参见前注[4],宋连斌书,第121页。
[34]参见前注[9],赵健书,第190页。
[35]参见前注[4],宋连斌书,第126-127页。
最新资讯
-
08-26 0
-
08-10 1
-
08-02 1
-
10-14 2
-
08-08 0
-
专利侵权诉讼中如何活用管辖权 ——专利侵权诉讼策略之一- 冯克法律师
09-2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