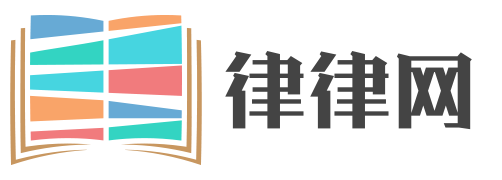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共用名称”之上产权争夺的经济学和法学分析——从“小肥羊”商标案谈起
发布时间:2019-12-07 00:00:15
</script>
【出处】《清华法学》2010年第4期。
【摘要】自我国2001年修订《商标法》接受了“第二含义理论”——即承认“共用名称”通过使用可以产生显著性,从而得以注册为商标(第11条第2款)——以来,相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一直不断,尤其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肥羊”商标案的发生,使得人们开始担忧,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而给经营者带来的激励,不免会引发过度投资,从而导致无效率的竞争和不公平的结果。但是,从“共用名称”之本质的经济分析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允许该标识注册为商标实际上是避免出现“公地灾难”的有效率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商标法上相关制度的设置,也不会产生学者们所担心的不公平的结果。
【英文摘要】Since the theory of "Secondary Meaning" was built into the amendment to the “Trademark Law of China”, we have seen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controversy around this topic in judicial practice. Especially, after the adjudication of the "Little Fat Lamb (Xiao Fei Yang)" case,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overinvestment”, thereby inducing the inefficient and unfair results, resulting from this newly adopted legal principle, which permits a “Common Term” to be registered as a trademark. However, based on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we argue that permitting the registration of a "Common Term" as a trademark will actually avoi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us promoting the overall social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other related legal mechanisms that supplement the functioning of trademark law, those unfair results will not necessarily occur as some scholars have worried about.
【关键词】共用名称;公地;第二含义;效率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引 言
,但该案所引发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场争论的缘起,又在于我国2001年对《商标法》的修订——该法第11条第2款规定,“共用名称”[2]“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应该说,商标法上的这一点规定,本意是对经营者所积累起来的商誉给予排他性的保护,但是,这一立法上的修改毕竟打开了争夺“共用名称”的口子,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多家经营者在使用、已经积累了一定商誉的“共用名称”,竞争者之间的争夺肯定会更加激烈,“小肥羊”商标案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争夺“共用名称”究竟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抑或是引发过度投资的行为?换言之,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私有化)究竟是提高效率、还是导致无效率竞争的做法?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来,应当建立“责任选购规则”来解决“共用名称”之上的产权争夺问题。[3]乍看起来,此观点很有道理,很多知识产权业内人士也是如此主张的——把大家一起打下的江山划归给一个人很不公平。但是,“责任选购规则”所要建立的补偿制度真的就比现行立法更有效率吗?另外,补偿的标准由谁提出?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如果补偿结果不为对方所接受,那么该争议如何解决?如此看来,“补偿制度”所谓的公平,并不是像其想象的那么容易实现。
本文借助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方法,就“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的合理性和效率这两方面展开探讨——通过分析“共用名称”的本质属性,结合“第二含义理论”的本旨与适用,论证了我国《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是避免出现“公地灾难”的有效率的做法、并不会导致过度投资,而补偿制度却并不能提高效率。
一、“共用名称”的私有化会导致“公地灾难”吗?
商品或服务的“共用名称”究竟是“公地”(open access)、抑或“共有财产”(communal property)?这是本文展开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在2001年《商标法》修订之前,诸如“小肥羊”之类的“共用名称”并不属于“公地”而是“共有财产”,相反,正是由于修法,才使得“共有财产”沦为“公地”,从而导致“公地灾难”。[4]然而,这一观点是否恰当呢?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对当代经济学界所谓的“公地”与“共有财产”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认识,进而,才能对2001年《商标法》的修订是否会导致“公地灾难”进行分析。
1、是“公地”还是“共有财产”?
自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发表《公地灾难》[5]一文以来,“公地灾难”一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其实,早在哈丁的文章发表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6]因此,或许可以说哈定的主要功绩在于让这个此前多少处于象牙塔之中的理论广泛进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然而,可能正是由于哈丁本人并非经济学家而是一位生态学家,他的这篇名作也给人们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准确来说,哈丁所谓的“灾难”并非发生于“公地(commons)”,而是发生于“开放地(open access)”。在英语中,“公地”的原意并非不设限制、人尽可入的“开放地”,而是“共有地”。在此后的文献中,虽然“公地灾难”一词被继承了下来,但“公地”的含义则发生了改变,即被视为“开放地”,同时,为视区别,原先意义上的“公地”被另一个词“共有财产(common property或communal property)”所替代。因此,今天当我们谈论“公地灾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描述一种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收成享益的产权形态,质言之,在此产权形态下,无人具有排除他人之权利。[7]而“共有财产”则是一种仅限于某一特定团体收成享益的产权形态,该团体的成员有权排除非团体成员的进入。所以,很显然,虽然二者均存在一个以上的财产享益人,但在是否具有排他的可能性上,二者则有所区别。[8]
厘清了“公地”与“共有财产”的区别,我们不难辨析我国《商标法》修订之前的 “共用名称”究竟处于何种产权形态之下。在“第二含义理论”未被立法所肯定之前,任何商业主体都可以使用“小肥羊”之类的共用名称,在先使用者无权排除在后者的使用。[9]很显然,“共用名称”在此背景下属于典型的“公地”状态,而2001年《商标法》的修改,系将“公地”在一定条件下予以私有化之举——原先“人尽可用”的“共用名称”有了被“专有”的可能性。概言之,修法之前,“共用名称”并非处于商标产权领地之外所划出的“保留地”,而是没有限制、人尽可入的“开放地”;而在2001年商标法中,该“开放地”可以有条件的私有化,而不是由“保留地”沦为了“开放地”。所以,认为“共用名称”系“共有财产”(即“共用名称”由多家企业共同共有)的观点并不成立,其不仅对“共用名称”的定性有误,而且对“共同共有”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正确,“共同共有”意味着权利主体的范围是封闭的,而“共用名称”之上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如此说来,“共用名称”在性质上无论是与美国昔日的“印第安人土地制度”、还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相似,“共用名称”之上并不存在“全体使用者”、随时可以有新的使用者加入,而后两者的所有者是特定的、任何非团体成员不得进入。[10]商标法修订之前“小肥羊”不能获得授权,恰恰不是源于该标识属于“保留地”,而是因为它是“开放地”,法律上认为不应赋予任何人以专有权。“保留地”有特定的、明确的权利人,他们可以排斥不属于这个团体的任何其他人,“共用名称”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性。
实际上,即使从民法上的所有权概念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与经济分析相同的结论。在民法理论上,所有权包括“共有”和“单独所有”这两种不同的形态,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所有权人是单个还是多个,而“共有”又区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所谓共有,系指“多数人所结合,但尚未形成法律人格之共同体,以团体组成员之资格而所有之状态”,[11]对照前文所述之经济学上“共有财产”的概念可知,法律领域中所认知的“共有”与其描述的是同一制度形态,也即是说,经济学上“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这一对概念,与民法上的“共有”和“单独所有”这两种所有权形态是分别对应的。
正因为如此,《商标法》修改之前区分“共用名称”与“注册商标”的背后观念,确实“不能套用欧陆民法体系中的所有权概念”[12],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其原因在于“共用名称”系“公地”而非“共有财产”。如果“共用名称”应被定性为“共有财产”的话,那么,其反而可以套用所有权制度中的“共有”概念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共用名称”属于共有财产,那么,该共有关系是何时形成的?共有人具体体现为什么样的团体?以“小肥羊”商标案来说,如果该标识属于“整个餐饮行业共同所有”,那么,其所有者的范围显然是不特定的,已使用者不能排斥新加入者,他们也不能被称之为“特定团体”。《商标法》修改前不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其明确的是任何使用“共用名称”的主体都不得排他,该条文绝没有包含“已使用者可以继续使用、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再使用该标识”之意。“共有财产”归属于特定团体,其实际上也是处于“专有”的状态,“共享和排他”不过是分别体现了全体所有者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因此,无论是从法律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学角度看,都不应将“共用名称”定性为“共有财产”。
2、“共用名称”之上的“公地灾难”是如何形成的
之所以有“公地灾难”之谓,是因为“公地”将导致过度投资,从而造成效率损失。借用经济学术语,“公地”造成的效率损失表现为“租金耗散”(rent dissipation)。简言之,就是由于人人都可以对某项财产收成享益,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人们为收成享益该财产而耗费的总成本与该财产带给人们的总收益相当,因此,这项财产没有给社会增加任何净收益。[13]假如我们将此财产划归一人所有,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净收益。对于该论断,我们将用下面这个示例来予以说明。而藉此我们也能较为直观的了解到,在“共用名称”之上,“公地灾难”是如何形成的。
当代的法经济学理论表明,商业标识作为一项财产,其价值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从而降低其搜寻信息的成本。而消费者节省了信息搜寻成本,就会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商品,因此,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节省的信息搜寻成本将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利润。[14]然而,为了获取此种利润,企业就需要耗费成本来培植商标。现假定:各家企业彼此相似,[15]每家都可以雇佣一个人来宣传某一商标,从而让一定数量的消费者节省信息搜寻成本(并愿意相应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且每一位消费者能够节省的信息搜寻成本均为10元;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向每一个进行商标宣传的受雇者支付65元的工资。[16]虽然,每位受雇宣传者获得的工资相同,但其究竟能为该商标吸引来多少顾客,则取决于此前的宣传者已经吸引了多数顾客。通常说来,随着宣传者人数的增加,尽管吸引的顾客人数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速度却会放缓,这是因为最容易被吸引的顾客总是被先受雇的宣传者所吸引,而留给在后受雇的宣传者的总是越来越难吸引的顾客,所以,在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在前的宣传者一般总能比在后的宣传者吸引来更多的顾客。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基于以上之假设,如下表[17]所示,我们将清楚地看到,随着使用同一商业标识的企业的数量增加,该标识之净价值是如何变化的:
(1)
企业总数(=宣传员总数) (2)
吸引顾客总数 (3)
总人工费(=(1)×65) (4)
行业总利润(=(2)×10) (5)
行业平均利润(=(4)/(1)) (6)
商标净价值(=(4)-(3))
0 0 0 0 —(即不存在) 0
1 10 65 100 100 35
2 19 130 190 95 60
3 27 195 270 90 75
4 34 260 340 85 80
5 40 325 400 80 75
6 45 390 450 75 60
7 49 455 490 70 35
8 52 520 520 65 0
对于某一家企业而言,只要使用该商标所需付出的成本(即65元人工费)[18]低于由此而带来的收益,其便会选择使用之。基于我们所假设的各企业具有同质性,故他们将均分行业总利润,也就是说,使用商标给每家企业所带来的收益等于行业平均利润。由上表可知,在此情况下,总共会有8家企业投入其中使用该商标,而此时商标的净价值为0,“公地灾难”由此产生。[19]
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商标产生最大的净价值,也就是说有4名宣传员进行宣传。倘若将标识授权某一家企业专有(即允许其通过注册而获得商标专用权),由于其他经营者不能再随便进入,则其会选择投入最佳数量的宣传员,以使商标的净价值最大化,亦即雇佣4名宣传员,正好符合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要求。[20]就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使用“共用名称”的某个企业是否决定申请注册,取决于已有多少家企业在使用该标识,只要这个数字低于8,他就有可能这么做,否则,让“共用名称”保持“公地”之状态,就很难阻止该标识的商标净价值变为0(如上表所示)。即使在“共用名称”获得注册之前使用该标识的企业已不止4家,但由于商标权人可以禁止再有其他企业进入,因而在效率上也比不去注册要高。[21]
由此可见,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对旧有做法的修改,使得“共用名称”之上避免出现“公地灾难”有了可能,[22]此举系将不明确的产权关系予以明确化、从而提高效率的做法,而并非是“改法制造出了一个财产权利的‘公共地’,也因此而制造了‘公地悲剧’”[23]的错误之举。
3、共有商标有效率还是独有商标有效率?
实际上,按照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确立的“共用名称”私有化之途径,如果多个企业之间进行协商、共同提起注册申请,那么,“共用名称”之上所可能产生的排他性商标专用权也可以由他们共有。不过,依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看,这种商标权共有的状态是否比独有更具效率呢?或者换言之,北京高院最终决定将“小肥羊”商标赋予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一家,而不认可各家小肥羊共有此商标的做法,是否“可能导致的是整体社会福利的急剧下降”呢?[24]我们不妨借助上面的表格,再作一番考察:
假定“共用名称”不再是公地、人尽可用,而是产生了商标专用权、专属于两家同质的企业,唯有他们可以使用,并且,此两家企业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以每人65元的成本雇佣宣传员培植商标。此时,如果两家能达成某种协议,将宣传员人数限于4人,并均分利润,则每家企业都可以收获40元(80/2)的商标净价值,比如双方可以约定各投入两名宣传员。然而,当一方(甲)按约投入两名宣传员时,假如另一方(乙)投入第3名宣传员,则其可以收获的商标净价值将变为45元,[25]所以,乙会有违反约定增加宣传员的动机。而倘若果真如此,则甲获得的商标净收益将变为30元。假如甲预见到乙存在这种违约动机,则其也会投入第3名宣传员,如此,则甲的收益仍是30元。[26]也就是说,将商标授予两家企业,而这两家企业又无法达成并执行投资协议的话,则市场中可能出现6名宣传员。[27]如此一来,商标的净价值则变为60元。反之,若将商标授予一家企业专用,则该企业会选择投入4名宣传员,从而令商标的净价值达到80元这个最大值。可见,如果商标权不专属于一家企业,那么,即便让两家企业共有一个商标仍会造成商标净价值的降低。[28]
由此,我们认为:,非但不会造成“整体社会福利的急剧下降”,恰恰相反,这样做可以避免由租金耗散造成的效率损失。这种效率上的比较,也恰好与实践中基本上是各家企业单独去申请注册“共用名称”的情况相符。当然,“共用名称”获得注册后,商标权人能否真正实现专有(独占),还取决于商标法律体系中的其他制度,如“在先使用权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详细分析。
二、为什么要求“共用名称”具备第二含义?
正是因为对“共用名称”之本质的认识不同,“‘共用名称’系共有财产”的观点认为,“公地灾难”源自“化公为私”,即“由于共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建立明确而且严格的法律标准,从而恰恰导致了产权不明。”[29]但是,这一点颇让人疑惑,因为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已产生了“第二含义”的“共用名称”获得界限明晰的产权,当然,所谓的标准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共用名称”已经产生了“第二含义”。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是以消费者的认知为基础而展开的,尽管司法实践都在力争做到客观化,但我们很清楚,想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设立明确、且完全客观的判断标准是不可能的,正如“驰名商标的判断标准”一样,如果因此就下结论——“缺乏明确而严格的标准就导致了产权不明”,恐怕并非妥当。
“第二含义”理论的产生,与商标注册中对显著性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都知道,某一标识具有显著性是其能够获得注册的实质要件,而所谓显著性,是识别性和区分性这两个层次之要求的综合体现。对于显著性的解读,相关著述颇丰,甚至提出了以量化的方法来认定之。但需注意的是,商标法对显著性只不过有最低要求,即普通消费者视某一标识为商标而非对商品或服务所进行的描述,量化的认定方式有可能无形中提高了商标注册的实质要件,,“不可能设定一个百分比,当视某一标识为商标的消费者达到这一比例时才认为该标识具有显著性”。[30]所以,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反证的方法来认定显著性,即排除不适合作为商标的标识,否则就认为其具有显著性。商标的显著性有“固有显著性”和“获得显著性”之分,它们的核心要义都在于,某一标识是否能使消费者发现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出处。[31]而作为获得显著性基础的“第二含义”,也就是指能产生某一标识与特定出处之间的关联,只不过这种关系是基于长期的使用而产生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使用”,“并非单纯地使用,而是作为产品出处的标志使用。”[32]
“共用名称”要想获得注册,就必须通过使用而产生“第二含义”,显然,在此之前,“共用名称”被认为是不具有固有显著性的,而“使用”是其产生“第二含义”、产生“获得显著性”的惟一途径。[33]实际上,从符号本身的角度来看,即使“共用名称”这种标识尚处于“公地”状态,其也并非不具有任何的“可识别性”,因此,单纯认为“不具有可识别性”是“共用名称”不能获得商标注册的原因,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而且,“共用名称”作为标识投入商业使用后同样具有商业价值,如果不给予保护、任其成为“公地”,会造成此种价值的耗散。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待“第二含义”的产生才能赋予商标专用权、而非直接授权呢?究竟如何认定“共用名称”产生了第二含义呢?以下试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一种回答。
将某一词汇认定为商标并赋予其商标专用权,实际上剥夺了授权之后其他商业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该词汇的权利,因此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在某一商业主体因为这种垄断而获得利益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成本是:其他商业主体必须寻找其他词汇来标识其产品。对于普通的商标词汇——特别是那些专为用作商标而创造出来的词汇——而言,这种对于他人语言使用的限制很小,相对商标专用权带来的收益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直接将此类词汇认定为商标并授予商标专用权具有经济合理性。[34]
但是,就“共用名称”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了。如果在“共用名称”刚刚被使用之初,就允许其获得商标注册,那么,注册人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为了以示区别,其宣传成本将不得不增加,诚如Landes和Posner所言,“其一旦被垄断,则会令其他商业主体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代价来寻找别的词汇标识其产品。”[35]因此,在“共用名称”被投入商业使用的初期,我们无法合理地估计出“赋予其商标专用权所能产生的收益”与“其他竞争者增加的成本”之间哪一项更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此种标识不断地被使用,我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信息,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估测“共用名称”被赋予商标专用权后可能产生的商业价值。[36]于是,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比较授予商标权的成本与收益孰重孰轻,避免没有效率地授权。质言之,对“共用名称”而言,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来判断其是否产生显著性(第二含义),可以降低错误授权的可能性。
在“共用名称”处于“公地”状态的期间,因为其具有的“共用”之性质,也因为其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可识别性”,可能会有同行业竞争者不断地投入其中,以求分享一份利益,从而导致租金耗散。这个期间越长,则可能投入“公地”的主体数量越多,租金耗散的程度也越严重,直至该标识的净价值为0。因此,给予“共用名称”商标授权的时机,应当选择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时。也就是说,一方面,让“共用名称”在一段期间的使用过程中处于“公地”状态可以降低错误授权的可能性,由此产生收益,而另一方面,该期间也会造成标识所具有的商业价值的耗散,由此产生成本;当使用达到某一时间点时,“共用名称”所可能增加的收益与因此而增加的成本相等时(即前述所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此时赋予商标专用权将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37]在此刻之前,“共用名称”为“公地”所产生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授权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在此刻之后,如果仍然让其处于“公地”状态,那么所产生的成本将大于其收益,授权的最佳时机已被延误。[38]由此可见,对所谓第二含义的认定,从效率角度看,实际上就是要选择这样一种最佳授权时机。
三、“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是“强者通吃”吗?
以上分析表明,相较于将“小肥羊”商标置于“公地”之境地,“明确产权、将其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增加社会福利。允许产生了“第二含义”的“共用名称”被注册为商标,实际上是将企业原来面临的“是否进入‘公地’的考量”变成了“是否参与争夺注册‘共用名称’的竞争”,因此,企业在考虑是否投入这场竞争时首先就要考虑,其如何才能成功获得注册。而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主张,“只要一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相对其他企业明显的业绩优势,他就可以借助商标法的这一条款将优势转化为胜势,独享原本只能与他人分享的财产资源”,[39]从该表述来看,“市场优势”被认为是“‘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的充分条件,即所谓“强者通吃”。对此,我们有个疑问,众所周知,“先申请原则”是商标法上决定商标专用权的归属首先应遵循的规则,那么,“强者通吃”怎就成了“共用名称”注册的惟一条件?紧接着我们还想问,是否只有“最强者”才能获得“共用名称”的注册?或者说,不是最强者,是否就不能通过“使用”而使该标识获得“显著性”?若如此,又该如何判断“具有明显的业绩优势”呢?[40]以下分述论之:
1、“在先申请”是第一位的
在商标申请和审查的整个过程中,“先申请原则”的适用是第一位的,即根据申请日来确立谁是在先申请者,然后才是“标识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判断。在这一问题上,“共用名称”申请注册时当然也不例外。对于该原则,我们不妨先根据实践中“商标申请与审查”的实际操作流程进行一下感性认识:(1)确定“申请日”,依次进行审查。当商标局受理一个申请案之后,会根据申请日的先后进行排序,以便于审查员依照先后顺序进行审查。如果在后的申请与在先的申请相同,若在先的申请已经获准,那么,根据“先申请原则”,在后申请会被驳回。(2)显著性的证明。在申请案中,申请人是无需提供关于“显著性”的证据或说明的,商标局的审查也只是根据商标检索来作出判断,审查人员不会、也无法涉及申请注册的标识的实际使用情况,所以,一旦涉及“共用名称”,审查人员通常会依据商标禁用条款予以驳回,申请人只有通过复审程序来证明其标识是具有显著性的。如果审查人员在后序的申请中发现还有相同的“共用名称”之注册申请,他们也会基于相同的理由而将之予以驳回,把争议的解决同样都交给复审程序、乃至最后的司法程序。[41]
从理论上讲,在商标争夺过程中,如果某标识的注册申请被驳回,任何人都可以就该标识而再次提出申请,只要其认为自己做好了充分准备(当然,这在实际中很少发生,因为任何一个申请案最终被驳回,都经历了审查、复审、诉讼的过程,一般不会有人就该标识再次提出注册申请了)。所以,“先申请原则”针对的是每一轮商标争夺中谁是最先申请者,如果一次争夺之后注册申请被驳回,那么下一轮争夺开始后仍然要看谁是最先申请者。换言之,驳回的决定作出后,就意味着下一轮争夺的开始,不能认为“先申请原则”针对的仅仅是第一轮争夺中的最先申请者,否则的话,就变成了任何一个标识都只能提起一次注册申请,一旦被驳回就不能再次申请了,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以“共用名称”来说,头一次因缺乏显著性而没有获得注册,并不意味着下一次申请时其仍然不具有显著性。
我们知道,在“小肥羊”商标的争夺战中,经历了多次拉锯,曾有多家企业提出过注册申请,但先后被驳回,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亦有过这样的遭遇,只不过在2001年商标法修订之后,该公司的又一次努力最后获得了成功。我们并不知道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是不是第一个提出注册申请的,也不知道每一轮争夺中有一家还是多家企业提出过申请,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该公司获胜的那一轮竞争中,只有其一家企业提出申请、或者其是最先提出申请的。因此,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在此案中的胜出,并未改变“在先申请”这一商标法的一般原则。
2、因使用而产生第二含义不是“强者通吃”
“第二含义”理论最早在《巴黎公约》中就有体现,即“在决定一个商标是否符合条件时,必须考虑所有实际情况,特别是商标使用时间的长短”。[42]美国1938年审结的“Armstrong Paint & Varnish Works v. Nu-Enamel Corp.”案是运用“第二含义”理论较早的、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法官在判决中表述到,“原告商标专用权的取得,系由于‘Nu-Enamel’已经成为表彰该商品为原告制造的事实。一个普通名词经过使用而具备上述性质,自然应成为商标而受保护。”[43]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所谓“第二含义”的产生,无非是法律对“消费者已经将相关词语或标志当作商标来看待”这一事实的确认。 案[44]中表明了认定“第二含义”的观点,“当申请人的某一商标在市场上使用一段时间后能够标示产品来源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人提供的同类产品,则该商标获得了显著性;有权机构必须对有关该商标标示产品出处并使之区别于他人产品的证据进行全面评估。”[45]TRIPS更是直截了当地确立了“第二含义”理论,其规定为:“如果标志不具有区别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固有属性,成员可以根据其通过使用取得的显著性,给予注册。”[46]归纳起来,所谓产生“第二含义”,就是指“共用名称”产生了能够将其所标示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新含义,而且,在消费者那里,这种标明产品来源的新含义,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共用名称”的原本所指——对产品本身的某种说明,也即是说,对于相关领域的公众而言,“第二含义”已经成为了该标识的首要含义。
由上可知,对“第二含义”的判断,应当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状态,[47]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公众心目中是怎样的认知状态”。所以,,“如果该标识不能向消费者暗示商品或服务来自一个特定的出处,则不能认为其产生了‘第二含义’。”[48]那么,哪些因素是判断消费者态度时的重要证据呢?在“Zatarain’s, Inc. v. Oak Grove Smokehouse, Inc.”案[49]中,主审法官认为,最有力的、能够证明“第二含义”已经产生的直接证据就是调查报告,即由专家证人所做的特定地区和范围的消费者对标识的态度。[50]除了调查报告这一直接证据之外,还有诸如广告的数量和形式 、销售额和使用的时间与方式等,都可以作为证明“第二含义”的间接证据。这一观点在“Aloe Crème Laboratories, Inc. v. Milsan, Inc., et al.”[51]、“Vision Center v. Opticks, Inc., Will Ross, Inc. and G. D. Searle & Co.”[52]及“Union Carbide Corp.v. Ever-ready Incorporated and Mark Gilbert”[53]等案件中都得到了体现。对此法官们还特别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因素的程度高低或强弱,而在于它们对改变“共用名称”的商业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54]另外,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因素都不能单独证明第二含义,它们必须组合在一起来证明消费者头脑中关于产品和产品来源之间的必要联系。[55]
对于上述这些司法实践中通常使用的标准,有学者指出这些标准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即“市场优势”。[56]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过于武断,理由如下:
其一,如果“第二含义”的核心判断标准就是“市场优势”的话,司法判案时就无所谓区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了,但实际上,在上述案例中,法官们认为“调查报告”是“most direct and persuasive way”,其余的诸如“销售额”、“广告”、“使用时间和方式”等证据不过是用来加强“调查报告”的说服力的。简言之,将“获得显著性”的判断标准抽象为“市场优势”与已有的司法实践并不相符。[57]
其二,所谓的“明显的业绩优势”究竟该如何判断?也即是说,申请注册者必须比其他使用者的经营业绩好多少才算是“明显”呢?显然,这是很难进行量化分析得;而且,一如上文所述,“第二含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应为“消费者是否已经将相关词语或标志当作商标来看待”,认为前述那些证据的核心为“市场优势”实际上是偏离了该理论的本质。
其三,“市场优势”实际上是拔高了“获得显著性”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只有具备了“市场优势”的最强者,消费者才会将其使用的“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对待。换言之,并不是只有“最强者”才能“获得显著性”,这里,有两个因素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一是世界各国在商标注册上通常采用“先申请原则”,如果业绩最优的企业并未申请注册,而在先提出申请的企业经营业绩也不错,其所提供的证据(尤其是调查报告)足以证明“消费者已经将其使用的‘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看待”,那么,其商标注册的申请就应当获得批准。而且在实践中,商标审查机构也是如此操作的,其并不会去寻找市场中的“最强者”。[58]二是“第二含义”的判断是基于特定的交易和市场范围,即前述“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仅仅是针对特定市场的消费者而言的,例如前引“Zatarain’s”案中对新奥尔良地区的消费者进行的调查,而对于在此范围之外的一般消费者、以及非商业领域来说,所可能得到的认知仍止于标识的本来含义(所谓的“第一含义”),因此,使用者是否为同行业经营者中的业绩最优者并不是判断“获得显著性”的核心要素。
其四,即使具备“市场优势”也不一定能得到肯定的结论,相反还可能得到否定的答案。因为,如果“共用名称”的描述性很强、且市场上使用该标识的企业众多,那么即使其中一家企业具有“市场优势”,恐怕也难以让消费者认识到该名称是作为一种产品出处而被使用(即消费者可能也不会将该“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对待)。又或者,如果某企业申请注册的“共用名称”仅其独家使用,那么“市场优势”的标准该如何适用呢?我们势必还要寻找其他的判断标准,最后可能还是回到了“某一标识是否产生了与特定出处之间的关系”这一标准。而“调查报告”则是直接针对“消费者态度”的标准,其最有力地、最直接地反映了消费者如何看待该标识,也不会造成不同情形下存在不同判断标准的情形。
综上所述,“第二含义”理论的确立,是对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的肯定,如果采取“强者通吃”的判定标准,实际上与这一理念是不相吻合的。而且,“第二含义”不等同于“强者通吃”,也就不会在“市场优势”不明确(几家竞争者的市场份额相差不大)时限于法律判断上的僵局。
四、“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会导致过度投资吗?
在“第二含义的判断标准就是市场优势”的观点看来,“北京高院的判决将‘小肥羊’的商标专用权全部划归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一家,剥夺了其他小肥羊公司继续使用‘小肥羊’商标的‘在先权利’,势必损害附着其上的合法的信赖利益”,[59]此即其所谓之“强者通吃”的源头。“强者通吃”最令人担心、或者说最不具有正当性之处在于,“共用名称私有化导致了法律规则激励下的过度投资”[60],也即是说,在“通吃”的“激励”下,商标权人将反过来打击作为竞争者的、其他使用该“共用名称”的经营者(即不允许这些经营者再使用该标识),以获取独占(独享“共用名称”上所累积的商业利益),因此,难免会引发多家企业竭尽所能的去争夺“共用名称”,因而导致“过度投资”。对此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共用名称”获得注册后的商标权效力范围有所夸大,实际上,对于因“第二含义”而获得注册的商标,商标法律体系中已经构建了相应的限制制度,如“在先使用权制度”、“合理使用制度”,以约束商标权的效力范围。作为一个理性的市场主体,投资于注册“共用名称”的争夺应该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其可预期的结果是,即使注册成功,权利人所获得之商标权的效力范围,也受到诸多的限制,除非能够走“驰名商标保护”的路径。概言之,商标权人试图通过打击其他使用者而获取独占的目的,其实是难以实现的。[61]
1、“在先使用权制度”会导致商标权“淡化”吗?
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服务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可以继续使用;但是,1993年7月1日后中断使用3年以上的,不得继续使用。”虽然该条款只是限于服务商标、还有时间点的要求,但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中肯定了“在先使用权制度”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小肥羊”案涉及的恰好是服务商标,因此,我们有理由在该案中适用这一制度。
认为“法律规则激励了过度投资”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在先使用权”制度,但表达了否定性的看法,理由在于,,因为这样会导致商标“淡化”。该学者及其他类似观点认为,商标法上不应当存在“在先使用权”制度,因为商标很容易因他人的使用而被“淡化”,尤其是基于“第二含义”而获得的商标权,更容易因“在先使用权”的存在而导致“显著性”丧失。[62]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原因有四:
首先,我国商标法上本已有“在先使用权”制度,不存在类推适用专利法上的这一制度的问题,法官们不该对法律如此不熟悉,而且,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的最终获胜,走的是“驰名商标保护”的路子,与单纯适用“在先使用权”制度显然不是一回事。
其次,“在先使用权”作为一种商标权限制制度,其本身就是侵权的例外,且该制度的适用以“善意”、“原有范围”为先决条件,这与“法官以判断是否一方侵权的方式对争议财产作出了产权界定”[63]并没有本质冲突,如果肯定被告有在先使用权,自然不构成侵权,反之,就是不认可被告的在先使用权。
再次,以“会淡化商标”为由而否定“在先使用权”制度未免太过武断,如果在先使用果真会淡化商标,那么这种“淡化”也发生在商标注册之前,在此情形下,申请者仍然获得了注册,说明在先使用并未影响标识的“显著性”,再加上前述之适用“在先使用权”的前提条件——“善意”、“原有范围”,“在先使用”的行为人数量、行为影响范围不会、也不能增加,因而其不会导致进一步的商标淡化。况且,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的考察,只是在商标注册阶段进行,显著性被“淡化”并不会导致注册商标被撤销,受影响的只是商标权的保护力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尼龙”、“Jeep”等商标,都已被淡化成商品通用名称了,但并不因此就撤销这些注册商标。
最后,商标权受保护的力度与该商标的显著性强弱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若有在先使用存在,商标的显著性就会弱一些,那么商标权受保护的力度也应当低一些,如果否定“在先使用权”的存在,等于是对显著性弱的商标给予了强保护,而且,那样的话,那些商标被他人抢注的企业就更加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行文至此,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学界和实务界都在有意或无意的扩大商标权的识别功能,似乎此主体与彼主体之间因商标权的存在就能界限分明,任何标识上的混淆可能,就是“搭便车”、就是对商标权的侵害,因而必须予以纠正。然而,商标权的识别功能似乎没有那么强,实践中消费者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凭藉商标就搜寻到特定的商品或服务,除非是驰名商标,普通商标权的反淡化能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强,否则,反淡化就有随意扩大化之嫌。我们通常说的商标权(非驰名商标)的排他性,就是体现为不得在相同或相似商品、服务上使用相同或相似标识,但在不相类似的商品上可以如此使用,仔细想想,这样的使用行为难道一丁点儿也不会“淡化”商标吗?试想,如果在不同商品上使用同一标识的企业数量多了,消费者仍然无法建立标识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特定联系。所以,我们不能一方面因“共用名称”私有化是一种法律规则激励下的垄断而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又随意扩大商标权的排除范围从而不适当地赋予其过强的垄断地位。
2、“合理使用”制度是抑制投资于“共用名称”之商标注册的另一重要因素
以上文提及之美国“Zatarain’s, Inc. v. Oak Grove Smokehouse, Inc.”案为例,,但法官接下来也认定,“当被控侵权之商标系公平地、善意地使用,只是用来向使用人描述当事人的商品、服务或它们的地理来源时,被告人可以进行‘合理使用’的抗辩”。[64]当然,抗辩的成立,取决于被告的使用行为针对的是该商标描述意义而非其商标意义。我国亦有此类案例发生,如“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诉四川长虹电器股份公司”的“HDTV”商标案[65]。概言之,所谓商标的合理使用,是指非商标权人基于描述或指示其商品或服务的需要,善意地在商业过程中使用了与商标权人的商标相同的标识;发生合理使用的商标,系文字商标、或包含文字的组合商标,而该使用行为是就这些文字在公共领域内的原始含义所作的一般形式上的使用(所谓对“第一含义”的使用),并且不超过合理的限度。
商标的合理使用包括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前者即是专门针对基于“第二含义”而获得显著性的商标,也就是说,由于“共用名称”的文字本身具有叙述性,因而商标权人不能妨碍他人在一般的叙述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汇,用来描述或说明他们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所谓“说明性、叙述性的使用意图”)。当然,这种使用以“不故意引起混淆或误认”为前提。应该说,合理使用是对商标权较有影响的一种限制制度,即使是驰名商标,若在侵权诉讼中面对合理使用之抗辩,也不敢保证“百战百胜”。所以,“共用名称”若能注册为商标,由于该标识同时含有所谓的第一含义和第二含义,商标权人应当能够预见到其权利遭遇合理使用的空间很大,从而影响其是否投资于申请注册“共用名称”的决定。
,其中第17条列举了属于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典型行为:“1、使用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行为;2、使用注册商标中直接表示商品的性质、用途、质量、主要原料、种类及其他特征的标志的行为;3、在销售商品时,为说明来源、指示用途等在必要范围内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4、规范使用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自己的企业名称及其字号的行为;5、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自己所在地的地名的行为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行为都是“共用名称”的第一含义所可能涉及的内容,足见合理使用的范畴之广,如果认为商标权人对这些情形不了解、其可以通过打击竞争者来获取对“共用名称”的独占,未免太过“世外桃源”了些。通常情况下,此类商标权的权利人只有尽可能地利用“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来排除竞争对手使用该“共用名称”,至于竞争对手能否实施合理使用,就要看法官能否认定其说明性、叙述性的使用意图了——不故意引起混淆或误认。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的胜利,同样也是遵循“驰名商标保护”的思路。[66]所以,“已经使用‘共用名称’的企业数量”、“‘共用名称’的叙述性的强弱”、“企业自身的实力”、“竞争对手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分析”、“适用驰名商标保护的可能性分析”等因素,都是企业决定是否投资于“共用名称”注册时的考察对象,正常的竞争无可避免,但不会导致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规则激励下的过度投资,除非这些企业对前述这些因素没有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综合以上两方面,既然“在先使用权”与“合理使用”制度客观存在、且其合理性已经得到论证,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在决定是否投入到“共用名称”注册的争夺之中时,就不可能不意识到,即使将来获得商标权,其权利范围会受到来自于这些制度的约束,从而做出理性的选择。其实,对于非“共用名称”的商标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企业并不会因“共用名称”可以私有化而在投资理性上与面对其他标识时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以将来之商标权的排他性强弱为依据的。如果认为法律规则上允许“共用名称”私有化就会导致市场主体不顾一切地去争夺,实际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在决定之前必然会考虑“获得第二含义认定的成本”、“获得商标权后的利益范围”等因素,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让“共用名称”保持为“公地”在效率上比允许其私有化更低,因此私有化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共用名称”的注册又有较大风险,所以,市场竞争者必然会在二者之间慎重取舍,故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发生“过度投资”的问题。
五、《商标法》第31条中“在先权利”的范围应如何理解?
认为“《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确立的‘共用名称’界权规则”并不妥当的学者还指出,北京高院判决将“小肥羊”的商标专用权归于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独家所有,是“剥夺了其他小肥羊公司继续使用‘小肥羊’商标的‘在先权利’”。[67]很显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究竟何谓《商标法》第31条所规定的“在先权利”、其范围何如?对此,该学者明确表示,希望将在先权利拓展到信赖利益或者更为一般的利益上去,他认为,“如果将‘合法’理解为‘民事合法’,那么对于‘权利’二字也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在特定法律条文中作出明确规定的‘有名’权利,而是也应包含其他符合民事法律制度保护原则的‘未名’权利,比如‘信赖利益’”。[68]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观点看,这种扩大“在先权利之范围”的做法,将会对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根据《商标法》第31条之规定,“不得侵害在先权利”表现为,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构成对在先权利的损害,则申请人将不能取得商标专用权,也就是说,在先权利人拥有一项排除商标专用权成立的特别权利(right to exclude)。因此,扩大在先权利人的范围也就意味着扩大拥有这种特别排除权者的范围。我们知道,如果某项商标注册申请涉及他人的在先权利,此时,申请人若还想取得商标专用权,其就必须与在先权利人进行磋商,以支付对价的方式获取其同意放弃行使这种排除权(即获取许可的方式)。[69]套用科斯定理以及磋商理论(bargain theory)的一般理论,[70]我们不难得知,商标专用权最终能否确立,将取决于进行这种磋商的交易成本之大小。由于交易成本通常随着参与磋商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71]所以,我们有理由预期,在扩大在先权利人的范围之后,需要进行的磋商增多,因而交易成本增加,故在他们之间更难达成协议,最终导致商标专用权难以成立。
对于“共用名称”的申请注册来说,任何使用该标识的企业都因此而享有某种商业利益(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没错的,但如果认为申请日之前使用过该标识的主体都因此而享有《商标法》第31条意义上的“在先权利”(如前述之“信赖利益”),则未免将“在先权利”的范围扩展的太大,造成前述之磋商成本过高,因而导致无人愿意在此情形下申请注册该“共用名称”,其结果就是让该标识继续沦于公地的处境,造成价值耗散。
在先权利人过多,也就是拥有排除权的人数过多,于是就可能产生所谓“反公地灾难”(tragedy of anticommons)的问题。[72]原先,“反公地灾难”是指一种由于众多主体拥有排除他人使用某项资源的权利,致使无人能够对该资源实施有效用益的现象,进而造成以利用不足为表现形式的资源浪费。在本文讨论的事例中,若拥有排除商标专用权之成立的“在先权利”过多,可能直接引起“商标专用权”这种法律资源无法被有效地用来保护有益的“共用名称”这一商业资源,由此间接导致该资源因得不到法律保护而陷入“公地灾难”。
由此可见,扩大在先权利人的范围以及由此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升高,可能使得有效率的商标专用权(即成立商标专用权,防止“公地灾难”的收益大于商标专用权给在先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之情形)无法成立,从而形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对于在先权利人的范围,应当立足于“成本—效益”分析而做出恰当的解释。
除了效率问题之外,我们从《商标法》第31条之立法本意出发,亦可得出“其他各家小肥羊公司在申请日之前使用‘小肥羊’标识而产生的商业利益并不构成《商标法》第31条意义上的‘在先权利’”的结论。笔者认为,“在先权利”的确立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即是为了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当商标权与在先权利发生冲突时,法律上应如何取舍。所谓权利冲突,是指权利实现的利益范畴发生交叉之情形,就《商标法》第31条而言,比如在先的著作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均有可能与在后的商标权发生冲突,因而立法上需要对此利益交叉之处做出权利归属上的安排。当然,可能与商标权冲突的不限于前述的著作权、人格权等,只要是权利实现的利益范畴与商标权存在交叉的可能,这样的权利应均属于“在先权利”的范围。明确了这一立法本意,我们再来看在先使用者基于“使用”而应享有的权益是否与在后获得的商标权有可能发生冲突?回答是否定的,“先用权”是对商标权的限制,商标法对“先用权”的肯定,就是出于对在先使用者利益的保护,在后的商标权是在“先用权”的利益范畴之外的专用权,因此,在先使用者的利益与商标权人的利益不会发生交叉(此处所言系应然的状态,在先使用者若突破原有使用范围则另当别论),也即是说,在先使用者的利益不会侵害在后的商标权,自无适用《商标法》第31条之必要。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在先权利之范围”的解析,是以权利冲突的概念为基础的,而与标识本身的样态无关,因此,无论是否属于申请注册“共用名称”,其“在先权利的范围”都是一样的,即“在先使用者应受保护之合法权益”非属此列。
更进一步而言,如果将“在先使用者的权益”放入“在先权利”的范畴,还会导致正当之商标资源的争夺受到阻碍,等于是使得未注册商标产生了排他性,而实际上,商标法上是允许对未注册商标展开正当之争夺的,当然,构成驰名商标的、或者不正当竞争的除外。举例来说:如果甲企业认为乙企业所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很有创意、很容易吸引顾客,而且乙还尚未注册,那么,依据商标法的规定,甲就该标识申请注册是没有障碍的(无论是不是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73];面对甲的抢注,乙要想“扳回劣势”,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申请认定驰名商标、从而“打掉”甲的商标注册,二是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起诉甲企业的行为系故意使消费者发生混淆或误认。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该商标专用权就应当归属于甲企业,这就是一场残酷的市场竞争,并没有什么不正当之处,对于在商标注册上过于懈怠的乙企业来说,这也是其在竞争中失败所应付出的代价。然而,如果“在先使用”形成《商标法》第31条意义上的“在先权利”,那么在后的商标注册就会被驳回,这样一来,“在先使用”就成了商标注册的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只要有在先使用者存在,尽管其所使用的标识并未进行注册,任何后来者也都不可能再去申请注册了。这样的结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符合现行法的规定,错误地使得未注册商标具有了排他性;二是限制了商标资源的正当竞争,鼓励了在先使用者在商标注册上的懈怠,其实并不利于市场竞争良性地、有序地展开。
六、补偿与否是否影响效率?
在质疑《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确立的“共用名称”界权规则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的“产权界定的责任规则”,按其主张,“共有财产转变为私有拆产的前提是,;同时,。”[74]将“责任规则”具体运用到“小肥羊”商标案中,该观点认为:,应要求其“按照某种方式补偿对小肥羊品牌价值具有重要贡献的其他企业”。[75]那么,引进这种补偿究竟会对效率产生何种影响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补偿损失——无论以何种标准进行,就既已产生的损失而言都只具有再分配的意义,而不会对效率产生影响。在“小肥羊”一案中,无论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是否给予其他公司补偿,这些公司此前为“小肥羊”商标而投入的成本都已经沉淀。从社会角度看,补偿与否只能改变由谁负担这些“沉淀成本”(sunk cost)的事实,而再也无法挽回这些成本——包括任何基于信赖而进行的投资。所以,如果补偿能够促进效率,则这种促进不会源自针对其他企业已经为“小肥羊”品牌价值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补偿,而将来自于防止(尚未发生的)产权向低效率的方向流动。换言之,假如其他企业使用该商标可以产生的净收益总和大于由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一家使用可以产生的净收益,则要求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补偿,就可以防止“小肥羊”商标权流向低价值的主体。从经济学角度看,其他企业丧失的净收益正是将权利赋予内蒙古小肥羊一家所带来的成本,通过补偿,我们可以令产权变动的得益方将产权变动的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有效率的产权配置。这也是征用(taking)规则要求合理补偿的经济学理由。[76]实际上,前述之观点正是基于类比征用规则而来。然而,本文讨论的主题与征用的情况有着本质差异,因此,补偿或许非但无助于实现上述促进效率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效率的减损。
征用是一种纯粹的产权移转,我们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来保证征用方对产权的估价一定高于被征用方,从而实现产权有效率的流动。因此,以补偿作为征用的条件,促使征用方将征用的成本内部化就可以防止——至少是减少——无效率的征用。然而,如前文所言,本文讨论的其实是将处于“公地”状态的产权明确化,从而避免“公地灾难”的问题。因此,在实质上我们讨论的并非产权移转的问题,而是产权性质转换的问题(由“公地”转变为私有财产)。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那样,至少,有关“公地灾难”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这种转换是有效率的——即使没有补偿规则也同样如此。
假如不论是否有补偿要求,都不会影响上述有效率的产权性质转换,那么,加入补偿规则后,。然而,补偿带来的问题似乎还不仅如此:首先,因为是“公地”而非特定群体的“共有”,故而处于“公地”状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享有,于是,补偿的对象至少在理论上成为了不特定的大众,而要向不特定的人进行补偿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以某种方式——例如在特定时间之前提起诉讼——确定补偿对象的范围,补偿仍将阻碍由“公地”到私有产权这一产权性质转换的过程。不难理解,当加入补偿条件后,最终取得私有产权的当事人必须向其他“公地”享有人作出补偿,于是,其取得私有产权的成本增加了,而这一增加的成本并不会使其取得的私有产权产生更多的收益——这种收益取决于市场需求与生产技术。换言之,补偿减少了个人(区别于社会)取得私有产权的净收益,从而将导致个人谋求私有产权的动力降低。与此相对,在加入补偿条件之后,其他原先享用“公地”却不准备谋求私有产权者(也就是被补偿者)的个人收益将随之增加——补偿流入了这些主体的口袋。于是,人们会有更大的动力到“公地”里分一杯羹。一方面是寻求将“公地”产权私有化的动力减小,另一方面则是跻身于“公地”的动力增大,补偿规则带来的这种此消彼长的激励作用将造成“公地”更有可能流于“公地”而不得转换为私有财产,从令“公地灾难”成为一种切实的灾难。
主张补偿制度的观点还提出,其他小肥羊公司失去“小肥羊”商标权后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竞争状态的问题,由此产生的“适应成本”也是将商标权归一家企业独有而产生的成本。[77]按照该观点的思路,似乎通过补偿,可以使这种“适应成本”内部化,进而确保有效率的产权移转。在产权的非自愿性移转过程中,适应成本确实是一项值得考虑的成本。不过,正如前文已经论证的那样,在“公地”这种产权形态之下,用益“公地”的各个主体最终都将面对租金耗散的结果。也就是说,“公地”的用益这者最终都要面临“公地”失去价值而不得不寻求其他资源的结局。质言之,就是“适应成本”早晚都会出现,所以,不给予补偿而直接将“公地”转换为私有财产,并没有生出新的“适应成本”来。[78]
另外,主张补偿制度的观点甚至还提到了所谓的“文化资产”问题,认为这也是需要通过补偿来解决的。该学者并未明确界定何为“文化资产”,而仅仅指出这种财产是“不可简单货币化的”、“包含辛勤劳动所凝聚的特殊感情等”。[79]对此,我们认为,若借用法经济学中比较常用的概念,这种“文化财产”似乎相当于商标的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与其客观(市场)价值相对。然而,在本文探讨的问题中,商标权属于法人,而法人只是一种由法律拟制的主体,并非真正的人,不知法人的“主观感受”、“特殊情感”究竟从何而来?倘使认为法人的“感受”、“情感”最终是构成法人的自然人之感受、情感,那么,将商标专用权归属于某一企业,并不妨碍其他企业员工的流动。简单说来,如果某位员工对企业失去的商标权含情脉脉、不忍割舍,则完全可以追随商标权一起流向别的企业。归根到底,即便普通的商标权转让,也不可能考虑出让企业某些员工个性化的主观感受这种因素,而只会服务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最终目标。因此,假如专为这种“文化财产”设立一项补偿规则,是否有些小题大作呢?
基于以上的法经济学分析,我们认为,建立所谓的“产权界定的责任规则”未必能够提高效率、改进社会福利。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基于这一规则而构建补偿制度似不足取。
结 语
“小肥羊”案引发的热烈探讨已经过去一阵子了,但笔者深感这一系列案件中所蕴含的法律问题,无论是方法论上的、抑或单纯法律制度上的,都还有深入研讨之必要。一如本文之标题,我们运用了法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共用名称”的性质出发,对“小肥羊”商标案中涉及的界权问题展开了分析,主要是就“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的效率与合理性这两方面展开探讨,从而论证了我国《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是避免出现“公地灾难”的有效率的做法、并不会导致过度投资。与此同时,本文对学者提出的“产权界定规则应当在单一的‘竞争规则’之外还要引入‘责任规则’”进行了质疑,以经济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补偿制度并不能提高效率。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
首先,“共用名称”系“公地”而非“共有财产”,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注册为商标是避免了、而不是导致了无效率的“公地灾难”;
其次,从效率的角度看,对“第二含义”的认定,实际上就是要选择一种最佳授权时机——即当“使用”达到某一时间点时,将“共用名称”认定为商标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此时赋予商标专用权将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
第三,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并非为“强者通吃”,而是对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进行肯定——消费者已将该“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看待;
第四,经营者应当知道,即使“共用名称”获得了商标注册,由于商标法上存在“先用权”、“合理使用”等商标权限制制度,使得通过打击其他使用者而获取独占的目的难以实现,除非可以走驰名商标保护的路径,因而,他们会理性的选择是否投资于其中;
第五,《商标法》第31条所确立的“在先权利”制度,是服务于“解决权利冲突”这一特定目的的,而“在先使用者的权益”与在后的商标专用权不存在权利冲突的问题,因而其并不能适用该条款,否则,正当之商标资源的争夺将受到阻碍,而且也使得未注册商标实际上产生了排他性。
最后,有关“公地灾难”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这种从“公地”到“私有财产”的转换是有效率的——即使没有补偿规则也同样如此,而构建“产权界定的责任规则”未必能够提高效率、改进社会福利。
综上所述,虽然本文支持现行商标法的规定而质疑“责任规则”的做法,但是,我们并无意于论证谁的观点更加正确,而只是试图实践学术之“争鸣”的本旨,希冀共同研讨以获增益。
【作者简介】
杨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张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法学与社会政策博士研究生(法经济学方向),哈佛大学法学院LLM,早稻田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注释】
[1]准确地说,“小肥羊”商标案是围绕“小肥羊LITTLE SHIP及图”的商标而展开争夺的一系列案件,历经6年。这些案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对于一个多家经营者都在使用的描述性商标,如何依据商标法上的“第二含义理论”来确定其产权归属。关于该案之详情,。
[2]《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规定的可以根据“第二含义理论”而获得商标注册的标识有两类,一为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另一为描述性标识(即表示商品或服务的原材料、功能、用途或其他特点的标识),为便于论述,本文遵循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惯常做法,将二者统称为“共用名称”。
[3]凌斌先生在其《肥羊之争:产权界定的法学和经济学思考——兼论<商标法>第9、11、31条》(《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4]参见前注3揭文第172、180页相关内容。
[5]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vol. 138, pp.1243-1248.
[6]此前经济学界研究相关问题的代表性文献如:Frank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vol. 38, pp. 582-606;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vol. 62, pp.124-142.
[7]所以,所谓“公地灾难”的确“不是源自共有财产这一产权制度本身”,但也绝不是“由于共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建立明确而且严格的法律标准”(参见前注3揭文,第180页),一如上文对哈丁之观点的解释,“公地灾难”根本就不是针对共有财产而言的,而是源于财产之“无主物”的状态。如果其真的是针对共有财产,而共有财产的属性是特定团体成员的共有,本身就具有排他性,那么,对其“化公为私”的“灾难”又从何谈起?
[8]See Thrainn Eggertsson, Open Access Versus Common Property, in Terry Anderson & Fred McChesney ed., Property Right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4.
[9]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形,例外的情形有两种:其一,构成不正当竞争;其二,某主体对该标识的使用足以使之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10]我国的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其特定性与明确性更是明显。
[1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12]前注3揭文,第172页。
[13]“公地灾难”的经典经济学模型见于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vol. 62, pp.124-142; Steven N.S. Cheung(张五常),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vol.13, pp.49-70.
[14]这是对商标权进行法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参见William Landes and Richard Posner, Trademark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7, vol. 30, pp.265-309.
[15]在此,我们借用了经典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享益财产的各个主体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也就是说他们面临同样的技术条件,因此具有相同的产能与成本,See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vol. 62, pp.124-142; Steven N.S. Cheung(张五常),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vol.13, pp.49-70.
[16]当然,培育商标不仅仅需要做宣传,更需要改进产品质量,而这一切都要耗费成本,在此,为论证之方便,我们以用于宣传的人工费指代所有此类成本。
[17]此表系依据Terry Anderson & Fred McChesney ed., Property Right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4, Table II.2修改而成。
[18]在某标识进入“专有”领域(即获得商标注册)之前,由于任何进入该行业的经营者均可以使用该标识,因而,为使顾客能够购买自己所生产的标注这一标识的商品或服务,每个经营者都必须支付一定的宣传成本,否则,顾客无法知道哪个经营者提供了标注该标识的商品或服务。
[19]“公地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进入者对已经在公地之中者产生的负外部性——即后续的进入会降低所有在先进入者的收益。
[20]如果我们仍旧坚持每家企业只能雇到1名宣传员的假设,那么,若不考虑交易成本,则拥有商标权的企业可以授权另外3家企业使用其商标,而授权使用费的总数最高可达60元((85-65)×3),再加上其自身使用商标的获益20元,其总收益仍为80元。
[21]这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申请注册的成本足够低,而事实上,实务中也的确如此。
[22]需要注意的是,如上面的例子所示,如果使用某一商标的每家企业都生产相同质量的产品,那么,商业标识能够减少信息搜寻成本的这一特性,并不因为其本身是否能成为注册商标而有所改变——只要它足以促进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也就是说,即使“共用名称”不能依法获得注册,该标识仍然可以产生正的价值。另外,“共用名称”为多家企业所共同使用的局面,还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如果某些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以图搭注重长远利益的优质企业的便车。很显然,这也是“共用名称”可能造成效率损失的一个原因,而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是在一定条件下减少此种效率损失的措施。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具体展开。
[23]参见前注3揭文,第180页。
[24]参见前注3揭文,第179页。
[25]此时,共有5名宣传员,由上表第(6)栏可知商标的净价值为75元,而乙投入3名宣传员,故其将取得商标净价值的3/5,也就是45元。
[26]此时,共有6名宣传员,由上表第(6)栏可知商标的净价值为60元,甲、乙投入3名宣传员,故将均分此净价值,也就是各获30元。
[27]这实际上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也是古诺双寡头竞争模型(Cournot duopoly)),而博弈双方各投入3名宣传员是此模型的古诺-纳什均衡点。在这样一个对称的静态博弈模型中(也就是双方需要同时作出策略选择),甲、乙都会进行如下推理:假如对方遵守约定雇佣2名宣传员,则我雇佣3名就比雇佣两名能获得更多收益;假如对方违反约定雇佣3名宣传员,则我雇佣3名也不会比雇佣2名少得收益,因此,无论如何我应当雇佣3名(雇佣3名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弱的支配性策略(weakly dominant strategy))。注意:无论对方选择雇佣2名还是3名宣传员,对甲、乙双方而言,选择雇佣3名以上的宣传员始终比选择雇佣3名的收益为少。有关于此的一个简单线性模型,可参见James Buchanan & Yong Yoon, Symmetric Tragedies: Commons and Anticommons, 4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8-9 (2000)。
[28]在此我们没有考虑维护商标权的成本问题。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与单个主体的私有相比,共同所有可能降低维护权利的成本,这是因为每一权利主体维护其权利的边际成本递增之故。例如,一家企业需要投入500元才能监控50%的商标盗用情况,而两家企业可能只需要各负担200元(总共400元)就可以监控50%的商标盗用情况。参见Dean Lueck, Common Property as an Egalitarian Share Contrac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5 (1994), pp.93-108。不过,,是否足以抵消共有产权导致的租金耗散,还有赖于对具体事例进行经验性的研究。
[29]参见前注3揭文,第180页。
[30]See Lloyd Schuhfabrik Meyer Gmbh v. Klijsen Handel BV, case V-342/97[1999], ETMR690, 699.
[31]所以,商标被认为是一种关系,是标识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特定的、指示性的符号关系。See Barton Beebe, 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rademark Law, 51 UCLA L. Rev. 621, 2004, p648.
[32]Jeremy Phillips, Trade Mark Law: A Practical Anat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9.
[33]“获得显著性”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描述性的丧失(实际上也不可能),而只是显著性超过了描述性。参见[美]米勒、戴维斯:《知识产权法》(英文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4]See William Landes and Richard Posner, Trademark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0, 1987, pp.273-274.
[35]同上注揭文,pp.291-292.
[36]在此,。不过,即便放松这一假定,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此种成本的信息也会增加,从而改进人们对它的估计。
[37]在此,与通常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我们假设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或恒定)。
[38]如果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此处所谓“授权的最佳时机已被延误”,也就是指,由于有太多的主体投入使用“共用名称”,导致其因使用而产生的显著性又丧失了。
[39]参见前注3揭文,第173页。
[40]在前注3揭文中,作者并不赞成“强者通吃”的结果,但其认为是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他认为,该条款的适用是在肯定“强者通吃”。本文此处正是质疑这一点,提出商标法的这一规定并不是采用“强者通吃”的标准。
[41]对于实务部门操作流程的介绍,是为了回答有些人可能会提出的两个质疑:其一,如果在先的申请并不具有显著性,而在后的申请才具有之,在先申请者显然不能获胜;其二,如果在先的申请是抢注他人的未注册商标,其是否能成功呢?此处所述之商标局关于商标注册的操作过程,笔者是通过详细咨询实务人员而得到的有关情况,特此表示感谢。当然,一如成例,文责由笔者承担。
[42]参见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页。
[43]曾陈明汝:《商标法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44]See Windsurfing Chiemsee Produktions- und Vertriebs GmbH v. Boots- und Segelzubehör Walter Huber and Franz Attenberger, Joined Cases C-108 and 109/97 [1999] ETMR 585.
[45]J. Thomas McCarthy, Trade Mark Law: A Practical Anat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9.
[46]参见TRIPS第15条第1项之规定。
[47]See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4th at Thomson West, 2001, pp.15-46; Robert P. Mergers, Peter S. Menell &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657.
[48]See “Coca-Cola Co. v. Koke Co. of America et al.”, 235 F. 408; 1916 U.S. Dist. LEXIS 1380.
[49]690 F. 2d 786, 5th Cir. 1983.
[50]在该案中,原告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其中一份是对新奥尔良地区100名女士(她们每月使用本案涉及的那一类商品至少3次以上)的调查,另一份是在新奥尔良地区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所作的调查。依据调查报告以及实际使用和广告这些间接证据,。See Robert P. Mergers, Peter S. Menell &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658.
[51]423 F.2d 845, 1970 U.S. App. LEXIS 10392.
[52]596 F.2d 111, 1979 U.S. App. LEXIS 14469.
[53]531 F.2d 366, 1976 U.S. App. LEXIS 13064.
[54]See Aloe Crème Laboratories, Inc. v. Milsan, Inc., et al., 423 F.2d 845, at 850, 1970 U.S. App. LEXIS 10392.
[55]Robert P. Mergers, Peter S. Menell &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p.657-658.
[56]参见前注3揭文,第173页。
[57]的确,在诸“小肥羊”商标案中,,但并不代表这样的司法操作是正确无疑的,显然,他们并未真正掌握确立“第二含义”理论的目的究竟为何,也不了解前述美国多年来的司法经验,结果造成了“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系“强者通吃”这一不被广为接受的结果,而实际上,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本不应该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被如此操作。
[58]即使某一企业在同业竞争者中并不具有明显的业绩优势,或者本行业中的确另有“龙头老大”存在,这也不妨碍该企业通过长期使用“共用名称”而使之产生第二含义,只要消费者能获得产品出处的信息即为已足。
[59]参见前注3揭文,第178页。
[60]参见前注3揭文,第179页。
[61]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应然、而非实然状态,因为其中还涉及企业、法官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实际上,笔者对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获得商标注册后反过头来打击其他使用“小肥羊”商标的竞争者并最终胜诉的判决是持否定看法的,法官无视“在先使用权制度”而判给了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以独占地位是不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据这样的判决就认为“相关企业会积极投身于注册‘共用名称’的争夺之中、从而导致过度投资”,以及“强者可以通吃”,是不能成立的。本文这一部分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而进行论述的。
[62]参见前注3揭文,第182页。
[63]同上注。
[64]同上注55揭书, p654.
[65]该案请参见孔祥俊、武建英、刘泽宇:《WI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法——原理·规则·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66]单纯“小肥羊”这三个字的中文文字商标,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的公告期刚刚于2009年9月14日才届满。
[67]参见前注3揭文,第178页。
[68]参见前注3揭文,第176页。
[69]如前所述,在商标审查的实践中,对标识的审查主要就是商标检索,即看看申请的标识是否与在先的商标相同或相似,所以,审查员不会、也无法去追究申请的标识是否会侵权他人的在先权利,因为这个范围实在太大,要求审查员主动审查,只会降低审查效率。在先权利的主张,完全依赖于权利人的自行主张。这就给了申请人与在先权利人进行磋商的空间,以使得商标注册能获得通过。
[70]See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4th ed.), Addison-Wesley, 2003, pp.78-80.
[71]同上注揭书,p93.
[72]“反公地灾难”这一概念最初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Heller基于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权配置之考察而提出(See Michael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1, p.621. ),最近,Heller教授又在其专著The Gridlock Economy (Basic Books, 2008)中对此理论进行了全面展开。不过,对于“反公地灾难”究竟是否与“公地灾难”有实质区别的另一种产权形态,还是“开放地”的一种表现形态,法经济学界似乎尚无定论。如本文所示,“反公地灾难”也可能是公地灾难的一种诱因,并且,其与“敲竹杠”(holdout)引发的交易成本问题也不无相似之处(参见Dean Lueck and Thomas Miceli, Property Law, in A. 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 ed.,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Elsevier (2007), pp.193, 238)。
[73]关于这一点,与前文所介绍的我国商标申请、审查的实际操作也是相吻合的。
[74]参见前注3揭文,第184页。
[75]参见前注3揭文,第186页。该文还提到,,但又认为此项条件非其文章主题所涉,因而未作展开,为此,我们也不准备深入讨论“公共利益”问题。
[76]有关征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参见Dean Lueck and Thomas Miceli, Property Law, in A. 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 ed.,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Elsevier, 2007, pp. 238-242.
[77]参见前注3揭文,第178页。
[78]当然,假如由共有财产向私有财产转换,则可能出现这种“适应成本”问题。不过,即便如此,要确定这种成本的大小以便给予补偿同样需要耗费成本,因此,补偿仍可能不是一种最有效率的规则。
[79]参见前注3揭文,第179页
【摘要】自我国2001年修订《商标法》接受了“第二含义理论”——即承认“共用名称”通过使用可以产生显著性,从而得以注册为商标(第11条第2款)——以来,相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一直不断,尤其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肥羊”商标案的发生,使得人们开始担忧,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而给经营者带来的激励,不免会引发过度投资,从而导致无效率的竞争和不公平的结果。但是,从“共用名称”之本质的经济分析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允许该标识注册为商标实际上是避免出现“公地灾难”的有效率的做法,而另一方面,商标法上相关制度的设置,也不会产生学者们所担心的不公平的结果。
【英文摘要】Since the theory of "Secondary Meaning" was built into the amendment to the “Trademark Law of China”, we have seen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controversy around this topic in judicial practice. Especially, after the adjudication of the "Little Fat Lamb (Xiao Fei Yang)" case, scholar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overinvestment”, thereby inducing the inefficient and unfair results, resulting from this newly adopted legal principle, which permits a “Common Term” to be registered as a trademark. However, based on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we argue that permitting the registration of a "Common Term" as a trademark will actually avoi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us promoting the overall social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other related legal mechanisms that supplement the functioning of trademark law, those unfair results will not necessarily occur as some scholars have worried about.
【关键词】共用名称;公地;第二含义;效率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引 言
,但该案所引发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场争论的缘起,又在于我国2001年对《商标法》的修订——该法第11条第2款规定,“共用名称”[2]“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应该说,商标法上的这一点规定,本意是对经营者所积累起来的商誉给予排他性的保护,但是,这一立法上的修改毕竟打开了争夺“共用名称”的口子,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多家经营者在使用、已经积累了一定商誉的“共用名称”,竞争者之间的争夺肯定会更加激烈,“小肥羊”商标案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争夺“共用名称”究竟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抑或是引发过度投资的行为?换言之,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私有化)究竟是提高效率、还是导致无效率竞争的做法?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来,应当建立“责任选购规则”来解决“共用名称”之上的产权争夺问题。[3]乍看起来,此观点很有道理,很多知识产权业内人士也是如此主张的——把大家一起打下的江山划归给一个人很不公平。但是,“责任选购规则”所要建立的补偿制度真的就比现行立法更有效率吗?另外,补偿的标准由谁提出?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如果补偿结果不为对方所接受,那么该争议如何解决?如此看来,“补偿制度”所谓的公平,并不是像其想象的那么容易实现。
本文借助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方法,就“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的合理性和效率这两方面展开探讨——通过分析“共用名称”的本质属性,结合“第二含义理论”的本旨与适用,论证了我国《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是避免出现“公地灾难”的有效率的做法、并不会导致过度投资,而补偿制度却并不能提高效率。
一、“共用名称”的私有化会导致“公地灾难”吗?
商品或服务的“共用名称”究竟是“公地”(open access)、抑或“共有财产”(communal property)?这是本文展开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在2001年《商标法》修订之前,诸如“小肥羊”之类的“共用名称”并不属于“公地”而是“共有财产”,相反,正是由于修法,才使得“共有财产”沦为“公地”,从而导致“公地灾难”。[4]然而,这一观点是否恰当呢?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对当代经济学界所谓的“公地”与“共有财产”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认识,进而,才能对2001年《商标法》的修订是否会导致“公地灾难”进行分析。
1、是“公地”还是“共有财产”?
自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发表《公地灾难》[5]一文以来,“公地灾难”一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其实,早在哈丁的文章发表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6]因此,或许可以说哈定的主要功绩在于让这个此前多少处于象牙塔之中的理论广泛进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然而,可能正是由于哈丁本人并非经济学家而是一位生态学家,他的这篇名作也给人们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准确来说,哈丁所谓的“灾难”并非发生于“公地(commons)”,而是发生于“开放地(open access)”。在英语中,“公地”的原意并非不设限制、人尽可入的“开放地”,而是“共有地”。在此后的文献中,虽然“公地灾难”一词被继承了下来,但“公地”的含义则发生了改变,即被视为“开放地”,同时,为视区别,原先意义上的“公地”被另一个词“共有财产(common property或communal property)”所替代。因此,今天当我们谈论“公地灾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描述一种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收成享益的产权形态,质言之,在此产权形态下,无人具有排除他人之权利。[7]而“共有财产”则是一种仅限于某一特定团体收成享益的产权形态,该团体的成员有权排除非团体成员的进入。所以,很显然,虽然二者均存在一个以上的财产享益人,但在是否具有排他的可能性上,二者则有所区别。[8]
厘清了“公地”与“共有财产”的区别,我们不难辨析我国《商标法》修订之前的 “共用名称”究竟处于何种产权形态之下。在“第二含义理论”未被立法所肯定之前,任何商业主体都可以使用“小肥羊”之类的共用名称,在先使用者无权排除在后者的使用。[9]很显然,“共用名称”在此背景下属于典型的“公地”状态,而2001年《商标法》的修改,系将“公地”在一定条件下予以私有化之举——原先“人尽可用”的“共用名称”有了被“专有”的可能性。概言之,修法之前,“共用名称”并非处于商标产权领地之外所划出的“保留地”,而是没有限制、人尽可入的“开放地”;而在2001年商标法中,该“开放地”可以有条件的私有化,而不是由“保留地”沦为了“开放地”。所以,认为“共用名称”系“共有财产”(即“共用名称”由多家企业共同共有)的观点并不成立,其不仅对“共用名称”的定性有误,而且对“共同共有”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正确,“共同共有”意味着权利主体的范围是封闭的,而“共用名称”之上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如此说来,“共用名称”在性质上无论是与美国昔日的“印第安人土地制度”、还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并不相似,“共用名称”之上并不存在“全体使用者”、随时可以有新的使用者加入,而后两者的所有者是特定的、任何非团体成员不得进入。[10]商标法修订之前“小肥羊”不能获得授权,恰恰不是源于该标识属于“保留地”,而是因为它是“开放地”,法律上认为不应赋予任何人以专有权。“保留地”有特定的、明确的权利人,他们可以排斥不属于这个团体的任何其他人,“共用名称”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性。
实际上,即使从民法上的所有权概念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与经济分析相同的结论。在民法理论上,所有权包括“共有”和“单独所有”这两种不同的形态,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所有权人是单个还是多个,而“共有”又区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所谓共有,系指“多数人所结合,但尚未形成法律人格之共同体,以团体组成员之资格而所有之状态”,[11]对照前文所述之经济学上“共有财产”的概念可知,法律领域中所认知的“共有”与其描述的是同一制度形态,也即是说,经济学上“共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这一对概念,与民法上的“共有”和“单独所有”这两种所有权形态是分别对应的。
正因为如此,《商标法》修改之前区分“共用名称”与“注册商标”的背后观念,确实“不能套用欧陆民法体系中的所有权概念”[12],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其原因在于“共用名称”系“公地”而非“共有财产”。如果“共用名称”应被定性为“共有财产”的话,那么,其反而可以套用所有权制度中的“共有”概念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共用名称”属于共有财产,那么,该共有关系是何时形成的?共有人具体体现为什么样的团体?以“小肥羊”商标案来说,如果该标识属于“整个餐饮行业共同所有”,那么,其所有者的范围显然是不特定的,已使用者不能排斥新加入者,他们也不能被称之为“特定团体”。《商标法》修改前不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其明确的是任何使用“共用名称”的主体都不得排他,该条文绝没有包含“已使用者可以继续使用、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再使用该标识”之意。“共有财产”归属于特定团体,其实际上也是处于“专有”的状态,“共享和排他”不过是分别体现了全体所有者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因此,无论是从法律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学角度看,都不应将“共用名称”定性为“共有财产”。
2、“共用名称”之上的“公地灾难”是如何形成的
之所以有“公地灾难”之谓,是因为“公地”将导致过度投资,从而造成效率损失。借用经济学术语,“公地”造成的效率损失表现为“租金耗散”(rent dissipation)。简言之,就是由于人人都可以对某项财产收成享益,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人们为收成享益该财产而耗费的总成本与该财产带给人们的总收益相当,因此,这项财产没有给社会增加任何净收益。[13]假如我们将此财产划归一人所有,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净收益。对于该论断,我们将用下面这个示例来予以说明。而藉此我们也能较为直观的了解到,在“共用名称”之上,“公地灾难”是如何形成的。
当代的法经济学理论表明,商业标识作为一项财产,其价值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从而降低其搜寻信息的成本。而消费者节省了信息搜寻成本,就会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商品,因此,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节省的信息搜寻成本将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利润。[14]然而,为了获取此种利润,企业就需要耗费成本来培植商标。现假定:各家企业彼此相似,[15]每家都可以雇佣一个人来宣传某一商标,从而让一定数量的消费者节省信息搜寻成本(并愿意相应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且每一位消费者能够节省的信息搜寻成本均为10元;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向每一个进行商标宣传的受雇者支付65元的工资。[16]虽然,每位受雇宣传者获得的工资相同,但其究竟能为该商标吸引来多少顾客,则取决于此前的宣传者已经吸引了多数顾客。通常说来,随着宣传者人数的增加,尽管吸引的顾客人数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速度却会放缓,这是因为最容易被吸引的顾客总是被先受雇的宣传者所吸引,而留给在后受雇的宣传者的总是越来越难吸引的顾客,所以,在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在前的宣传者一般总能比在后的宣传者吸引来更多的顾客。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基于以上之假设,如下表[17]所示,我们将清楚地看到,随着使用同一商业标识的企业的数量增加,该标识之净价值是如何变化的:
(1)
企业总数(=宣传员总数) (2)
吸引顾客总数 (3)
总人工费(=(1)×65) (4)
行业总利润(=(2)×10) (5)
行业平均利润(=(4)/(1)) (6)
商标净价值(=(4)-(3))
0 0 0 0 —(即不存在) 0
1 10 65 100 100 35
2 19 130 190 95 60
3 27 195 270 90 75
4 34 260 340 85 80
5 40 325 400 80 75
6 45 390 450 75 60
7 49 455 490 70 35
8 52 520 520 65 0
对于某一家企业而言,只要使用该商标所需付出的成本(即65元人工费)[18]低于由此而带来的收益,其便会选择使用之。基于我们所假设的各企业具有同质性,故他们将均分行业总利润,也就是说,使用商标给每家企业所带来的收益等于行业平均利润。由上表可知,在此情况下,总共会有8家企业投入其中使用该商标,而此时商标的净价值为0,“公地灾难”由此产生。[19]
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商标产生最大的净价值,也就是说有4名宣传员进行宣传。倘若将标识授权某一家企业专有(即允许其通过注册而获得商标专用权),由于其他经营者不能再随便进入,则其会选择投入最佳数量的宣传员,以使商标的净价值最大化,亦即雇佣4名宣传员,正好符合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要求。[20]就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使用“共用名称”的某个企业是否决定申请注册,取决于已有多少家企业在使用该标识,只要这个数字低于8,他就有可能这么做,否则,让“共用名称”保持“公地”之状态,就很难阻止该标识的商标净价值变为0(如上表所示)。即使在“共用名称”获得注册之前使用该标识的企业已不止4家,但由于商标权人可以禁止再有其他企业进入,因而在效率上也比不去注册要高。[21]
由此可见,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对旧有做法的修改,使得“共用名称”之上避免出现“公地灾难”有了可能,[22]此举系将不明确的产权关系予以明确化、从而提高效率的做法,而并非是“改法制造出了一个财产权利的‘公共地’,也因此而制造了‘公地悲剧’”[23]的错误之举。
3、共有商标有效率还是独有商标有效率?
实际上,按照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确立的“共用名称”私有化之途径,如果多个企业之间进行协商、共同提起注册申请,那么,“共用名称”之上所可能产生的排他性商标专用权也可以由他们共有。不过,依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看,这种商标权共有的状态是否比独有更具效率呢?或者换言之,北京高院最终决定将“小肥羊”商标赋予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一家,而不认可各家小肥羊共有此商标的做法,是否“可能导致的是整体社会福利的急剧下降”呢?[24]我们不妨借助上面的表格,再作一番考察:
假定“共用名称”不再是公地、人尽可用,而是产生了商标专用权、专属于两家同质的企业,唯有他们可以使用,并且,此两家企业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以每人65元的成本雇佣宣传员培植商标。此时,如果两家能达成某种协议,将宣传员人数限于4人,并均分利润,则每家企业都可以收获40元(80/2)的商标净价值,比如双方可以约定各投入两名宣传员。然而,当一方(甲)按约投入两名宣传员时,假如另一方(乙)投入第3名宣传员,则其可以收获的商标净价值将变为45元,[25]所以,乙会有违反约定增加宣传员的动机。而倘若果真如此,则甲获得的商标净收益将变为30元。假如甲预见到乙存在这种违约动机,则其也会投入第3名宣传员,如此,则甲的收益仍是30元。[26]也就是说,将商标授予两家企业,而这两家企业又无法达成并执行投资协议的话,则市场中可能出现6名宣传员。[27]如此一来,商标的净价值则变为60元。反之,若将商标授予一家企业专用,则该企业会选择投入4名宣传员,从而令商标的净价值达到80元这个最大值。可见,如果商标权不专属于一家企业,那么,即便让两家企业共有一个商标仍会造成商标净价值的降低。[28]
由此,我们认为:,非但不会造成“整体社会福利的急剧下降”,恰恰相反,这样做可以避免由租金耗散造成的效率损失。这种效率上的比较,也恰好与实践中基本上是各家企业单独去申请注册“共用名称”的情况相符。当然,“共用名称”获得注册后,商标权人能否真正实现专有(独占),还取决于商标法律体系中的其他制度,如“在先使用权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详细分析。
二、为什么要求“共用名称”具备第二含义?
正是因为对“共用名称”之本质的认识不同,“‘共用名称’系共有财产”的观点认为,“公地灾难”源自“化公为私”,即“由于共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建立明确而且严格的法律标准,从而恰恰导致了产权不明。”[29]但是,这一点颇让人疑惑,因为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已产生了“第二含义”的“共用名称”获得界限明晰的产权,当然,所谓的标准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共用名称”已经产生了“第二含义”。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是以消费者的认知为基础而展开的,尽管司法实践都在力争做到客观化,但我们很清楚,想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设立明确、且完全客观的判断标准是不可能的,正如“驰名商标的判断标准”一样,如果因此就下结论——“缺乏明确而严格的标准就导致了产权不明”,恐怕并非妥当。
“第二含义”理论的产生,与商标注册中对显著性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都知道,某一标识具有显著性是其能够获得注册的实质要件,而所谓显著性,是识别性和区分性这两个层次之要求的综合体现。对于显著性的解读,相关著述颇丰,甚至提出了以量化的方法来认定之。但需注意的是,商标法对显著性只不过有最低要求,即普通消费者视某一标识为商标而非对商品或服务所进行的描述,量化的认定方式有可能无形中提高了商标注册的实质要件,,“不可能设定一个百分比,当视某一标识为商标的消费者达到这一比例时才认为该标识具有显著性”。[30]所以,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反证的方法来认定显著性,即排除不适合作为商标的标识,否则就认为其具有显著性。商标的显著性有“固有显著性”和“获得显著性”之分,它们的核心要义都在于,某一标识是否能使消费者发现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出处。[31]而作为获得显著性基础的“第二含义”,也就是指能产生某一标识与特定出处之间的关联,只不过这种关系是基于长期的使用而产生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使用”,“并非单纯地使用,而是作为产品出处的标志使用。”[32]
“共用名称”要想获得注册,就必须通过使用而产生“第二含义”,显然,在此之前,“共用名称”被认为是不具有固有显著性的,而“使用”是其产生“第二含义”、产生“获得显著性”的惟一途径。[33]实际上,从符号本身的角度来看,即使“共用名称”这种标识尚处于“公地”状态,其也并非不具有任何的“可识别性”,因此,单纯认为“不具有可识别性”是“共用名称”不能获得商标注册的原因,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而且,“共用名称”作为标识投入商业使用后同样具有商业价值,如果不给予保护、任其成为“公地”,会造成此种价值的耗散。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待“第二含义”的产生才能赋予商标专用权、而非直接授权呢?究竟如何认定“共用名称”产生了第二含义呢?以下试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一种回答。
将某一词汇认定为商标并赋予其商标专用权,实际上剥夺了授权之后其他商业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该词汇的权利,因此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在某一商业主体因为这种垄断而获得利益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成本是:其他商业主体必须寻找其他词汇来标识其产品。对于普通的商标词汇——特别是那些专为用作商标而创造出来的词汇——而言,这种对于他人语言使用的限制很小,相对商标专用权带来的收益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直接将此类词汇认定为商标并授予商标专用权具有经济合理性。[34]
但是,就“共用名称”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了。如果在“共用名称”刚刚被使用之初,就允许其获得商标注册,那么,注册人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为了以示区别,其宣传成本将不得不增加,诚如Landes和Posner所言,“其一旦被垄断,则会令其他商业主体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代价来寻找别的词汇标识其产品。”[35]因此,在“共用名称”被投入商业使用的初期,我们无法合理地估计出“赋予其商标专用权所能产生的收益”与“其他竞争者增加的成本”之间哪一项更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此种标识不断地被使用,我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信息,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估测“共用名称”被赋予商标专用权后可能产生的商业价值。[36]于是,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比较授予商标权的成本与收益孰重孰轻,避免没有效率地授权。质言之,对“共用名称”而言,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来判断其是否产生显著性(第二含义),可以降低错误授权的可能性。
在“共用名称”处于“公地”状态的期间,因为其具有的“共用”之性质,也因为其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可识别性”,可能会有同行业竞争者不断地投入其中,以求分享一份利益,从而导致租金耗散。这个期间越长,则可能投入“公地”的主体数量越多,租金耗散的程度也越严重,直至该标识的净价值为0。因此,给予“共用名称”商标授权的时机,应当选择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时。也就是说,一方面,让“共用名称”在一段期间的使用过程中处于“公地”状态可以降低错误授权的可能性,由此产生收益,而另一方面,该期间也会造成标识所具有的商业价值的耗散,由此产生成本;当使用达到某一时间点时,“共用名称”所可能增加的收益与因此而增加的成本相等时(即前述所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此时赋予商标专用权将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37]在此刻之前,“共用名称”为“公地”所产生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授权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在此刻之后,如果仍然让其处于“公地”状态,那么所产生的成本将大于其收益,授权的最佳时机已被延误。[38]由此可见,对所谓第二含义的认定,从效率角度看,实际上就是要选择这样一种最佳授权时机。
三、“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是“强者通吃”吗?
以上分析表明,相较于将“小肥羊”商标置于“公地”之境地,“明确产权、将其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增加社会福利。允许产生了“第二含义”的“共用名称”被注册为商标,实际上是将企业原来面临的“是否进入‘公地’的考量”变成了“是否参与争夺注册‘共用名称’的竞争”,因此,企业在考虑是否投入这场竞争时首先就要考虑,其如何才能成功获得注册。而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主张,“只要一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相对其他企业明显的业绩优势,他就可以借助商标法的这一条款将优势转化为胜势,独享原本只能与他人分享的财产资源”,[39]从该表述来看,“市场优势”被认为是“‘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的充分条件,即所谓“强者通吃”。对此,我们有个疑问,众所周知,“先申请原则”是商标法上决定商标专用权的归属首先应遵循的规则,那么,“强者通吃”怎就成了“共用名称”注册的惟一条件?紧接着我们还想问,是否只有“最强者”才能获得“共用名称”的注册?或者说,不是最强者,是否就不能通过“使用”而使该标识获得“显著性”?若如此,又该如何判断“具有明显的业绩优势”呢?[40]以下分述论之:
1、“在先申请”是第一位的
在商标申请和审查的整个过程中,“先申请原则”的适用是第一位的,即根据申请日来确立谁是在先申请者,然后才是“标识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判断。在这一问题上,“共用名称”申请注册时当然也不例外。对于该原则,我们不妨先根据实践中“商标申请与审查”的实际操作流程进行一下感性认识:(1)确定“申请日”,依次进行审查。当商标局受理一个申请案之后,会根据申请日的先后进行排序,以便于审查员依照先后顺序进行审查。如果在后的申请与在先的申请相同,若在先的申请已经获准,那么,根据“先申请原则”,在后申请会被驳回。(2)显著性的证明。在申请案中,申请人是无需提供关于“显著性”的证据或说明的,商标局的审查也只是根据商标检索来作出判断,审查人员不会、也无法涉及申请注册的标识的实际使用情况,所以,一旦涉及“共用名称”,审查人员通常会依据商标禁用条款予以驳回,申请人只有通过复审程序来证明其标识是具有显著性的。如果审查人员在后序的申请中发现还有相同的“共用名称”之注册申请,他们也会基于相同的理由而将之予以驳回,把争议的解决同样都交给复审程序、乃至最后的司法程序。[41]
从理论上讲,在商标争夺过程中,如果某标识的注册申请被驳回,任何人都可以就该标识而再次提出申请,只要其认为自己做好了充分准备(当然,这在实际中很少发生,因为任何一个申请案最终被驳回,都经历了审查、复审、诉讼的过程,一般不会有人就该标识再次提出注册申请了)。所以,“先申请原则”针对的是每一轮商标争夺中谁是最先申请者,如果一次争夺之后注册申请被驳回,那么下一轮争夺开始后仍然要看谁是最先申请者。换言之,驳回的决定作出后,就意味着下一轮争夺的开始,不能认为“先申请原则”针对的仅仅是第一轮争夺中的最先申请者,否则的话,就变成了任何一个标识都只能提起一次注册申请,一旦被驳回就不能再次申请了,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以“共用名称”来说,头一次因缺乏显著性而没有获得注册,并不意味着下一次申请时其仍然不具有显著性。
我们知道,在“小肥羊”商标的争夺战中,经历了多次拉锯,曾有多家企业提出过注册申请,但先后被驳回,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亦有过这样的遭遇,只不过在2001年商标法修订之后,该公司的又一次努力最后获得了成功。我们并不知道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是不是第一个提出注册申请的,也不知道每一轮争夺中有一家还是多家企业提出过申请,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该公司获胜的那一轮竞争中,只有其一家企业提出申请、或者其是最先提出申请的。因此,内蒙古小肥羊公司在此案中的胜出,并未改变“在先申请”这一商标法的一般原则。
2、因使用而产生第二含义不是“强者通吃”
“第二含义”理论最早在《巴黎公约》中就有体现,即“在决定一个商标是否符合条件时,必须考虑所有实际情况,特别是商标使用时间的长短”。[42]美国1938年审结的“Armstrong Paint & Varnish Works v. Nu-Enamel Corp.”案是运用“第二含义”理论较早的、影响最大的案件之一,法官在判决中表述到,“原告商标专用权的取得,系由于‘Nu-Enamel’已经成为表彰该商品为原告制造的事实。一个普通名词经过使用而具备上述性质,自然应成为商标而受保护。”[43]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所谓“第二含义”的产生,无非是法律对“消费者已经将相关词语或标志当作商标来看待”这一事实的确认。 案[44]中表明了认定“第二含义”的观点,“当申请人的某一商标在市场上使用一段时间后能够标示产品来源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人提供的同类产品,则该商标获得了显著性;有权机构必须对有关该商标标示产品出处并使之区别于他人产品的证据进行全面评估。”[45]TRIPS更是直截了当地确立了“第二含义”理论,其规定为:“如果标志不具有区别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固有属性,成员可以根据其通过使用取得的显著性,给予注册。”[46]归纳起来,所谓产生“第二含义”,就是指“共用名称”产生了能够将其所标示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新含义,而且,在消费者那里,这种标明产品来源的新含义,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共用名称”的原本所指——对产品本身的某种说明,也即是说,对于相关领域的公众而言,“第二含义”已经成为了该标识的首要含义。
由上可知,对“第二含义”的判断,应当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心理状态,[47]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公众心目中是怎样的认知状态”。所以,,“如果该标识不能向消费者暗示商品或服务来自一个特定的出处,则不能认为其产生了‘第二含义’。”[48]那么,哪些因素是判断消费者态度时的重要证据呢?在“Zatarain’s, Inc. v. Oak Grove Smokehouse, Inc.”案[49]中,主审法官认为,最有力的、能够证明“第二含义”已经产生的直接证据就是调查报告,即由专家证人所做的特定地区和范围的消费者对标识的态度。[50]除了调查报告这一直接证据之外,还有诸如广告的数量和形式 、销售额和使用的时间与方式等,都可以作为证明“第二含义”的间接证据。这一观点在“Aloe Crème Laboratories, Inc. v. Milsan, Inc., et al.”[51]、“Vision Center v. Opticks, Inc., Will Ross, Inc. and G. D. Searle & Co.”[52]及“Union Carbide Corp.v. Ever-ready Incorporated and Mark Gilbert”[53]等案件中都得到了体现。对此法官们还特别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因素的程度高低或强弱,而在于它们对改变“共用名称”的商业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54]另外,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因素都不能单独证明第二含义,它们必须组合在一起来证明消费者头脑中关于产品和产品来源之间的必要联系。[55]
对于上述这些司法实践中通常使用的标准,有学者指出这些标准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即“市场优势”。[56]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过于武断,理由如下:
其一,如果“第二含义”的核心判断标准就是“市场优势”的话,司法判案时就无所谓区分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了,但实际上,在上述案例中,法官们认为“调查报告”是“most direct and persuasive way”,其余的诸如“销售额”、“广告”、“使用时间和方式”等证据不过是用来加强“调查报告”的说服力的。简言之,将“获得显著性”的判断标准抽象为“市场优势”与已有的司法实践并不相符。[57]
其二,所谓的“明显的业绩优势”究竟该如何判断?也即是说,申请注册者必须比其他使用者的经营业绩好多少才算是“明显”呢?显然,这是很难进行量化分析得;而且,一如上文所述,“第二含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应为“消费者是否已经将相关词语或标志当作商标来看待”,认为前述那些证据的核心为“市场优势”实际上是偏离了该理论的本质。
其三,“市场优势”实际上是拔高了“获得显著性”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只有具备了“市场优势”的最强者,消费者才会将其使用的“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对待。换言之,并不是只有“最强者”才能“获得显著性”,这里,有两个因素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一是世界各国在商标注册上通常采用“先申请原则”,如果业绩最优的企业并未申请注册,而在先提出申请的企业经营业绩也不错,其所提供的证据(尤其是调查报告)足以证明“消费者已经将其使用的‘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看待”,那么,其商标注册的申请就应当获得批准。而且在实践中,商标审查机构也是如此操作的,其并不会去寻找市场中的“最强者”。[58]二是“第二含义”的判断是基于特定的交易和市场范围,即前述“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仅仅是针对特定市场的消费者而言的,例如前引“Zatarain’s”案中对新奥尔良地区的消费者进行的调查,而对于在此范围之外的一般消费者、以及非商业领域来说,所可能得到的认知仍止于标识的本来含义(所谓的“第一含义”),因此,使用者是否为同行业经营者中的业绩最优者并不是判断“获得显著性”的核心要素。
其四,即使具备“市场优势”也不一定能得到肯定的结论,相反还可能得到否定的答案。因为,如果“共用名称”的描述性很强、且市场上使用该标识的企业众多,那么即使其中一家企业具有“市场优势”,恐怕也难以让消费者认识到该名称是作为一种产品出处而被使用(即消费者可能也不会将该“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对待)。又或者,如果某企业申请注册的“共用名称”仅其独家使用,那么“市场优势”的标准该如何适用呢?我们势必还要寻找其他的判断标准,最后可能还是回到了“某一标识是否产生了与特定出处之间的关系”这一标准。而“调查报告”则是直接针对“消费者态度”的标准,其最有力地、最直接地反映了消费者如何看待该标识,也不会造成不同情形下存在不同判断标准的情形。
综上所述,“第二含义”理论的确立,是对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的肯定,如果采取“强者通吃”的判定标准,实际上与这一理念是不相吻合的。而且,“第二含义”不等同于“强者通吃”,也就不会在“市场优势”不明确(几家竞争者的市场份额相差不大)时限于法律判断上的僵局。
四、“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会导致过度投资吗?
在“第二含义的判断标准就是市场优势”的观点看来,“北京高院的判决将‘小肥羊’的商标专用权全部划归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一家,剥夺了其他小肥羊公司继续使用‘小肥羊’商标的‘在先权利’,势必损害附着其上的合法的信赖利益”,[59]此即其所谓之“强者通吃”的源头。“强者通吃”最令人担心、或者说最不具有正当性之处在于,“共用名称私有化导致了法律规则激励下的过度投资”[60],也即是说,在“通吃”的“激励”下,商标权人将反过来打击作为竞争者的、其他使用该“共用名称”的经营者(即不允许这些经营者再使用该标识),以获取独占(独享“共用名称”上所累积的商业利益),因此,难免会引发多家企业竭尽所能的去争夺“共用名称”,因而导致“过度投资”。对此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共用名称”获得注册后的商标权效力范围有所夸大,实际上,对于因“第二含义”而获得注册的商标,商标法律体系中已经构建了相应的限制制度,如“在先使用权制度”、“合理使用制度”,以约束商标权的效力范围。作为一个理性的市场主体,投资于注册“共用名称”的争夺应该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其可预期的结果是,即使注册成功,权利人所获得之商标权的效力范围,也受到诸多的限制,除非能够走“驰名商标保护”的路径。概言之,商标权人试图通过打击其他使用者而获取独占的目的,其实是难以实现的。[61]
1、“在先使用权制度”会导致商标权“淡化”吗?
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4条规定:“连续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服务商标,与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服务上已注册的服务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可以继续使用;但是,1993年7月1日后中断使用3年以上的,不得继续使用。”虽然该条款只是限于服务商标、还有时间点的要求,但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中肯定了“在先使用权制度”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小肥羊”案涉及的恰好是服务商标,因此,我们有理由在该案中适用这一制度。
认为“法律规则激励了过度投资”的学者也注意到了“在先使用权”制度,但表达了否定性的看法,理由在于,,因为这样会导致商标“淡化”。该学者及其他类似观点认为,商标法上不应当存在“在先使用权”制度,因为商标很容易因他人的使用而被“淡化”,尤其是基于“第二含义”而获得的商标权,更容易因“在先使用权”的存在而导致“显著性”丧失。[62]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原因有四:
首先,我国商标法上本已有“在先使用权”制度,不存在类推适用专利法上的这一制度的问题,法官们不该对法律如此不熟悉,而且,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的最终获胜,走的是“驰名商标保护”的路子,与单纯适用“在先使用权”制度显然不是一回事。
其次,“在先使用权”作为一种商标权限制制度,其本身就是侵权的例外,且该制度的适用以“善意”、“原有范围”为先决条件,这与“法官以判断是否一方侵权的方式对争议财产作出了产权界定”[63]并没有本质冲突,如果肯定被告有在先使用权,自然不构成侵权,反之,就是不认可被告的在先使用权。
再次,以“会淡化商标”为由而否定“在先使用权”制度未免太过武断,如果在先使用果真会淡化商标,那么这种“淡化”也发生在商标注册之前,在此情形下,申请者仍然获得了注册,说明在先使用并未影响标识的“显著性”,再加上前述之适用“在先使用权”的前提条件——“善意”、“原有范围”,“在先使用”的行为人数量、行为影响范围不会、也不能增加,因而其不会导致进一步的商标淡化。况且,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的考察,只是在商标注册阶段进行,显著性被“淡化”并不会导致注册商标被撤销,受影响的只是商标权的保护力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尼龙”、“Jeep”等商标,都已被淡化成商品通用名称了,但并不因此就撤销这些注册商标。
最后,商标权受保护的力度与该商标的显著性强弱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若有在先使用存在,商标的显著性就会弱一些,那么商标权受保护的力度也应当低一些,如果否定“在先使用权”的存在,等于是对显著性弱的商标给予了强保护,而且,那样的话,那些商标被他人抢注的企业就更加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行文至此,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学界和实务界都在有意或无意的扩大商标权的识别功能,似乎此主体与彼主体之间因商标权的存在就能界限分明,任何标识上的混淆可能,就是“搭便车”、就是对商标权的侵害,因而必须予以纠正。然而,商标权的识别功能似乎没有那么强,实践中消费者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凭藉商标就搜寻到特定的商品或服务,除非是驰名商标,普通商标权的反淡化能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强,否则,反淡化就有随意扩大化之嫌。我们通常说的商标权(非驰名商标)的排他性,就是体现为不得在相同或相似商品、服务上使用相同或相似标识,但在不相类似的商品上可以如此使用,仔细想想,这样的使用行为难道一丁点儿也不会“淡化”商标吗?试想,如果在不同商品上使用同一标识的企业数量多了,消费者仍然无法建立标识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的特定联系。所以,我们不能一方面因“共用名称”私有化是一种法律规则激励下的垄断而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又随意扩大商标权的排除范围从而不适当地赋予其过强的垄断地位。
2、“合理使用”制度是抑制投资于“共用名称”之商标注册的另一重要因素
以上文提及之美国“Zatarain’s, Inc. v. Oak Grove Smokehouse, Inc.”案为例,,但法官接下来也认定,“当被控侵权之商标系公平地、善意地使用,只是用来向使用人描述当事人的商品、服务或它们的地理来源时,被告人可以进行‘合理使用’的抗辩”。[64]当然,抗辩的成立,取决于被告的使用行为针对的是该商标描述意义而非其商标意义。我国亦有此类案例发生,如“厦门华侨电子企业有限公司诉四川长虹电器股份公司”的“HDTV”商标案[65]。概言之,所谓商标的合理使用,是指非商标权人基于描述或指示其商品或服务的需要,善意地在商业过程中使用了与商标权人的商标相同的标识;发生合理使用的商标,系文字商标、或包含文字的组合商标,而该使用行为是就这些文字在公共领域内的原始含义所作的一般形式上的使用(所谓对“第一含义”的使用),并且不超过合理的限度。
商标的合理使用包括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前者即是专门针对基于“第二含义”而获得显著性的商标,也就是说,由于“共用名称”的文字本身具有叙述性,因而商标权人不能妨碍他人在一般的叙述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汇,用来描述或说明他们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所谓“说明性、叙述性的使用意图”)。当然,这种使用以“不故意引起混淆或误认”为前提。应该说,合理使用是对商标权较有影响的一种限制制度,即使是驰名商标,若在侵权诉讼中面对合理使用之抗辩,也不敢保证“百战百胜”。所以,“共用名称”若能注册为商标,由于该标识同时含有所谓的第一含义和第二含义,商标权人应当能够预见到其权利遭遇合理使用的空间很大,从而影响其是否投资于申请注册“共用名称”的决定。
,其中第17条列举了属于叙述性合理使用的典型行为:“1、使用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行为;2、使用注册商标中直接表示商品的性质、用途、质量、主要原料、种类及其他特征的标志的行为;3、在销售商品时,为说明来源、指示用途等在必要范围内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4、规范使用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自己的企业名称及其字号的行为;5、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自己所在地的地名的行为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行为都是“共用名称”的第一含义所可能涉及的内容,足见合理使用的范畴之广,如果认为商标权人对这些情形不了解、其可以通过打击竞争者来获取对“共用名称”的独占,未免太过“世外桃源”了些。通常情况下,此类商标权的权利人只有尽可能地利用“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来排除竞争对手使用该“共用名称”,至于竞争对手能否实施合理使用,就要看法官能否认定其说明性、叙述性的使用意图了——不故意引起混淆或误认。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的胜利,同样也是遵循“驰名商标保护”的思路。[66]所以,“已经使用‘共用名称’的企业数量”、“‘共用名称’的叙述性的强弱”、“企业自身的实力”、“竞争对手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分析”、“适用驰名商标保护的可能性分析”等因素,都是企业决定是否投资于“共用名称”注册时的考察对象,正常的竞争无可避免,但不会导致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规则激励下的过度投资,除非这些企业对前述这些因素没有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综合以上两方面,既然“在先使用权”与“合理使用”制度客观存在、且其合理性已经得到论证,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在决定是否投入到“共用名称”注册的争夺之中时,就不可能不意识到,即使将来获得商标权,其权利范围会受到来自于这些制度的约束,从而做出理性的选择。其实,对于非“共用名称”的商标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企业并不会因“共用名称”可以私有化而在投资理性上与面对其他标识时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以将来之商标权的排他性强弱为依据的。如果认为法律规则上允许“共用名称”私有化就会导致市场主体不顾一切地去争夺,实际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在决定之前必然会考虑“获得第二含义认定的成本”、“获得商标权后的利益范围”等因素,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让“共用名称”保持为“公地”在效率上比允许其私有化更低,因此私有化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共用名称”的注册又有较大风险,所以,市场竞争者必然会在二者之间慎重取舍,故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发生“过度投资”的问题。
五、《商标法》第31条中“在先权利”的范围应如何理解?
认为“《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确立的‘共用名称’界权规则”并不妥当的学者还指出,北京高院判决将“小肥羊”的商标专用权归于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独家所有,是“剥夺了其他小肥羊公司继续使用‘小肥羊’商标的‘在先权利’”。[67]很显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究竟何谓《商标法》第31条所规定的“在先权利”、其范围何如?对此,该学者明确表示,希望将在先权利拓展到信赖利益或者更为一般的利益上去,他认为,“如果将‘合法’理解为‘民事合法’,那么对于‘权利’二字也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在特定法律条文中作出明确规定的‘有名’权利,而是也应包含其他符合民事法律制度保护原则的‘未名’权利,比如‘信赖利益’”。[68]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观点看,这种扩大“在先权利之范围”的做法,将会对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根据《商标法》第31条之规定,“不得侵害在先权利”表现为,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专用权可能构成对在先权利的损害,则申请人将不能取得商标专用权,也就是说,在先权利人拥有一项排除商标专用权成立的特别权利(right to exclude)。因此,扩大在先权利人的范围也就意味着扩大拥有这种特别排除权者的范围。我们知道,如果某项商标注册申请涉及他人的在先权利,此时,申请人若还想取得商标专用权,其就必须与在先权利人进行磋商,以支付对价的方式获取其同意放弃行使这种排除权(即获取许可的方式)。[69]套用科斯定理以及磋商理论(bargain theory)的一般理论,[70]我们不难得知,商标专用权最终能否确立,将取决于进行这种磋商的交易成本之大小。由于交易成本通常随着参与磋商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71]所以,我们有理由预期,在扩大在先权利人的范围之后,需要进行的磋商增多,因而交易成本增加,故在他们之间更难达成协议,最终导致商标专用权难以成立。
对于“共用名称”的申请注册来说,任何使用该标识的企业都因此而享有某种商业利益(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没错的,但如果认为申请日之前使用过该标识的主体都因此而享有《商标法》第31条意义上的“在先权利”(如前述之“信赖利益”),则未免将“在先权利”的范围扩展的太大,造成前述之磋商成本过高,因而导致无人愿意在此情形下申请注册该“共用名称”,其结果就是让该标识继续沦于公地的处境,造成价值耗散。
在先权利人过多,也就是拥有排除权的人数过多,于是就可能产生所谓“反公地灾难”(tragedy of anticommons)的问题。[72]原先,“反公地灾难”是指一种由于众多主体拥有排除他人使用某项资源的权利,致使无人能够对该资源实施有效用益的现象,进而造成以利用不足为表现形式的资源浪费。在本文讨论的事例中,若拥有排除商标专用权之成立的“在先权利”过多,可能直接引起“商标专用权”这种法律资源无法被有效地用来保护有益的“共用名称”这一商业资源,由此间接导致该资源因得不到法律保护而陷入“公地灾难”。
由此可见,扩大在先权利人的范围以及由此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升高,可能使得有效率的商标专用权(即成立商标专用权,防止“公地灾难”的收益大于商标专用权给在先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之情形)无法成立,从而形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出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对于在先权利人的范围,应当立足于“成本—效益”分析而做出恰当的解释。
除了效率问题之外,我们从《商标法》第31条之立法本意出发,亦可得出“其他各家小肥羊公司在申请日之前使用‘小肥羊’标识而产生的商业利益并不构成《商标法》第31条意义上的‘在先权利’”的结论。笔者认为,“在先权利”的确立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即是为了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当商标权与在先权利发生冲突时,法律上应如何取舍。所谓权利冲突,是指权利实现的利益范畴发生交叉之情形,就《商标法》第31条而言,比如在先的著作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均有可能与在后的商标权发生冲突,因而立法上需要对此利益交叉之处做出权利归属上的安排。当然,可能与商标权冲突的不限于前述的著作权、人格权等,只要是权利实现的利益范畴与商标权存在交叉的可能,这样的权利应均属于“在先权利”的范围。明确了这一立法本意,我们再来看在先使用者基于“使用”而应享有的权益是否与在后获得的商标权有可能发生冲突?回答是否定的,“先用权”是对商标权的限制,商标法对“先用权”的肯定,就是出于对在先使用者利益的保护,在后的商标权是在“先用权”的利益范畴之外的专用权,因此,在先使用者的利益与商标权人的利益不会发生交叉(此处所言系应然的状态,在先使用者若突破原有使用范围则另当别论),也即是说,在先使用者的利益不会侵害在后的商标权,自无适用《商标法》第31条之必要。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在先权利之范围”的解析,是以权利冲突的概念为基础的,而与标识本身的样态无关,因此,无论是否属于申请注册“共用名称”,其“在先权利的范围”都是一样的,即“在先使用者应受保护之合法权益”非属此列。
更进一步而言,如果将“在先使用者的权益”放入“在先权利”的范畴,还会导致正当之商标资源的争夺受到阻碍,等于是使得未注册商标产生了排他性,而实际上,商标法上是允许对未注册商标展开正当之争夺的,当然,构成驰名商标的、或者不正当竞争的除外。举例来说:如果甲企业认为乙企业所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很有创意、很容易吸引顾客,而且乙还尚未注册,那么,依据商标法的规定,甲就该标识申请注册是没有障碍的(无论是不是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73];面对甲的抢注,乙要想“扳回劣势”,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申请认定驰名商标、从而“打掉”甲的商标注册,二是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起诉甲企业的行为系故意使消费者发生混淆或误认。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该商标专用权就应当归属于甲企业,这就是一场残酷的市场竞争,并没有什么不正当之处,对于在商标注册上过于懈怠的乙企业来说,这也是其在竞争中失败所应付出的代价。然而,如果“在先使用”形成《商标法》第31条意义上的“在先权利”,那么在后的商标注册就会被驳回,这样一来,“在先使用”就成了商标注册的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只要有在先使用者存在,尽管其所使用的标识并未进行注册,任何后来者也都不可能再去申请注册了。这样的结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符合现行法的规定,错误地使得未注册商标具有了排他性;二是限制了商标资源的正当竞争,鼓励了在先使用者在商标注册上的懈怠,其实并不利于市场竞争良性地、有序地展开。
六、补偿与否是否影响效率?
在质疑《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确立的“共用名称”界权规则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的“产权界定的责任规则”,按其主张,“共有财产转变为私有拆产的前提是,;同时,。”[74]将“责任规则”具体运用到“小肥羊”商标案中,该观点认为:,应要求其“按照某种方式补偿对小肥羊品牌价值具有重要贡献的其他企业”。[75]那么,引进这种补偿究竟会对效率产生何种影响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补偿损失——无论以何种标准进行,就既已产生的损失而言都只具有再分配的意义,而不会对效率产生影响。在“小肥羊”一案中,无论内蒙古小肥羊公司是否给予其他公司补偿,这些公司此前为“小肥羊”商标而投入的成本都已经沉淀。从社会角度看,补偿与否只能改变由谁负担这些“沉淀成本”(sunk cost)的事实,而再也无法挽回这些成本——包括任何基于信赖而进行的投资。所以,如果补偿能够促进效率,则这种促进不会源自针对其他企业已经为“小肥羊”品牌价值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补偿,而将来自于防止(尚未发生的)产权向低效率的方向流动。换言之,假如其他企业使用该商标可以产生的净收益总和大于由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一家使用可以产生的净收益,则要求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补偿,就可以防止“小肥羊”商标权流向低价值的主体。从经济学角度看,其他企业丧失的净收益正是将权利赋予内蒙古小肥羊一家所带来的成本,通过补偿,我们可以令产权变动的得益方将产权变动的成本内部化,从而实现有效率的产权配置。这也是征用(taking)规则要求合理补偿的经济学理由。[76]实际上,前述之观点正是基于类比征用规则而来。然而,本文讨论的主题与征用的情况有着本质差异,因此,补偿或许非但无助于实现上述促进效率的作用,而且可能导致效率的减损。
征用是一种纯粹的产权移转,我们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来保证征用方对产权的估价一定高于被征用方,从而实现产权有效率的流动。因此,以补偿作为征用的条件,促使征用方将征用的成本内部化就可以防止——至少是减少——无效率的征用。然而,如前文所言,本文讨论的其实是将处于“公地”状态的产权明确化,从而避免“公地灾难”的问题。因此,在实质上我们讨论的并非产权移转的问题,而是产权性质转换的问题(由“公地”转变为私有财产)。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的那样,至少,有关“公地灾难”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这种转换是有效率的——即使没有补偿规则也同样如此。
假如不论是否有补偿要求,都不会影响上述有效率的产权性质转换,那么,加入补偿规则后,。然而,补偿带来的问题似乎还不仅如此:首先,因为是“公地”而非特定群体的“共有”,故而处于“公地”状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享有,于是,补偿的对象至少在理论上成为了不特定的大众,而要向不特定的人进行补偿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以某种方式——例如在特定时间之前提起诉讼——确定补偿对象的范围,补偿仍将阻碍由“公地”到私有产权这一产权性质转换的过程。不难理解,当加入补偿条件后,最终取得私有产权的当事人必须向其他“公地”享有人作出补偿,于是,其取得私有产权的成本增加了,而这一增加的成本并不会使其取得的私有产权产生更多的收益——这种收益取决于市场需求与生产技术。换言之,补偿减少了个人(区别于社会)取得私有产权的净收益,从而将导致个人谋求私有产权的动力降低。与此相对,在加入补偿条件之后,其他原先享用“公地”却不准备谋求私有产权者(也就是被补偿者)的个人收益将随之增加——补偿流入了这些主体的口袋。于是,人们会有更大的动力到“公地”里分一杯羹。一方面是寻求将“公地”产权私有化的动力减小,另一方面则是跻身于“公地”的动力增大,补偿规则带来的这种此消彼长的激励作用将造成“公地”更有可能流于“公地”而不得转换为私有财产,从令“公地灾难”成为一种切实的灾难。
主张补偿制度的观点还提出,其他小肥羊公司失去“小肥羊”商标权后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竞争状态的问题,由此产生的“适应成本”也是将商标权归一家企业独有而产生的成本。[77]按照该观点的思路,似乎通过补偿,可以使这种“适应成本”内部化,进而确保有效率的产权移转。在产权的非自愿性移转过程中,适应成本确实是一项值得考虑的成本。不过,正如前文已经论证的那样,在“公地”这种产权形态之下,用益“公地”的各个主体最终都将面对租金耗散的结果。也就是说,“公地”的用益这者最终都要面临“公地”失去价值而不得不寻求其他资源的结局。质言之,就是“适应成本”早晚都会出现,所以,不给予补偿而直接将“公地”转换为私有财产,并没有生出新的“适应成本”来。[78]
另外,主张补偿制度的观点甚至还提到了所谓的“文化资产”问题,认为这也是需要通过补偿来解决的。该学者并未明确界定何为“文化资产”,而仅仅指出这种财产是“不可简单货币化的”、“包含辛勤劳动所凝聚的特殊感情等”。[79]对此,我们认为,若借用法经济学中比较常用的概念,这种“文化财产”似乎相当于商标的主观价值(subjective value),与其客观(市场)价值相对。然而,在本文探讨的问题中,商标权属于法人,而法人只是一种由法律拟制的主体,并非真正的人,不知法人的“主观感受”、“特殊情感”究竟从何而来?倘使认为法人的“感受”、“情感”最终是构成法人的自然人之感受、情感,那么,将商标专用权归属于某一企业,并不妨碍其他企业员工的流动。简单说来,如果某位员工对企业失去的商标权含情脉脉、不忍割舍,则完全可以追随商标权一起流向别的企业。归根到底,即便普通的商标权转让,也不可能考虑出让企业某些员工个性化的主观感受这种因素,而只会服务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最终目标。因此,假如专为这种“文化财产”设立一项补偿规则,是否有些小题大作呢?
基于以上的法经济学分析,我们认为,建立所谓的“产权界定的责任规则”未必能够提高效率、改进社会福利。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基于这一规则而构建补偿制度似不足取。
结 语
“小肥羊”案引发的热烈探讨已经过去一阵子了,但笔者深感这一系列案件中所蕴含的法律问题,无论是方法论上的、抑或单纯法律制度上的,都还有深入研讨之必要。一如本文之标题,我们运用了法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共用名称”的性质出发,对“小肥羊”商标案中涉及的界权问题展开了分析,主要是就“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的效率与合理性这两方面展开探讨,从而论证了我国《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是避免出现“公地灾难”的有效率的做法、并不会导致过度投资。与此同时,本文对学者提出的“产权界定规则应当在单一的‘竞争规则’之外还要引入‘责任规则’”进行了质疑,以经济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补偿制度并不能提高效率。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观点包括:
首先,“共用名称”系“公地”而非“共有财产”,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注册为商标是避免了、而不是导致了无效率的“公地灾难”;
其次,从效率的角度看,对“第二含义”的认定,实际上就是要选择一种最佳授权时机——即当“使用”达到某一时间点时,将“共用名称”认定为商标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此时赋予商标专用权将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
第三,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并非为“强者通吃”,而是对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进行肯定——消费者已将该“共用名称”作为商标来看待;
第四,经营者应当知道,即使“共用名称”获得了商标注册,由于商标法上存在“先用权”、“合理使用”等商标权限制制度,使得通过打击其他使用者而获取独占的目的难以实现,除非可以走驰名商标保护的路径,因而,他们会理性的选择是否投资于其中;
第五,《商标法》第31条所确立的“在先权利”制度,是服务于“解决权利冲突”这一特定目的的,而“在先使用者的权益”与在后的商标专用权不存在权利冲突的问题,因而其并不能适用该条款,否则,正当之商标资源的争夺将受到阻碍,而且也使得未注册商标实际上产生了排他性。
最后,有关“公地灾难”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允许“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这种从“公地”到“私有财产”的转换是有效率的——即使没有补偿规则也同样如此,而构建“产权界定的责任规则”未必能够提高效率、改进社会福利。
综上所述,虽然本文支持现行商标法的规定而质疑“责任规则”的做法,但是,我们并无意于论证谁的观点更加正确,而只是试图实践学术之“争鸣”的本旨,希冀共同研讨以获增益。
【作者简介】
杨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张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法学与社会政策博士研究生(法经济学方向),哈佛大学法学院LLM,早稻田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注释】
[1]准确地说,“小肥羊”商标案是围绕“小肥羊LITTLE SHIP及图”的商标而展开争夺的一系列案件,历经6年。这些案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对于一个多家经营者都在使用的描述性商标,如何依据商标法上的“第二含义理论”来确定其产权归属。关于该案之详情,。
[2]《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所规定的可以根据“第二含义理论”而获得商标注册的标识有两类,一为商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另一为描述性标识(即表示商品或服务的原材料、功能、用途或其他特点的标识),为便于论述,本文遵循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惯常做法,将二者统称为“共用名称”。
[3]凌斌先生在其《肥羊之争:产权界定的法学和经济学思考——兼论<商标法>第9、11、31条》(《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4]参见前注3揭文第172、180页相关内容。
[5]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vol. 138, pp.1243-1248.
[6]此前经济学界研究相关问题的代表性文献如:Frank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vol. 38, pp. 582-606;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vol. 62, pp.124-142.
[7]所以,所谓“公地灾难”的确“不是源自共有财产这一产权制度本身”,但也绝不是“由于共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建立明确而且严格的法律标准”(参见前注3揭文,第180页),一如上文对哈丁之观点的解释,“公地灾难”根本就不是针对共有财产而言的,而是源于财产之“无主物”的状态。如果其真的是针对共有财产,而共有财产的属性是特定团体成员的共有,本身就具有排他性,那么,对其“化公为私”的“灾难”又从何谈起?
[8]See Thrainn Eggertsson, Open Access Versus Common Property, in Terry Anderson & Fred McChesney ed., Property Right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4.
[9]当然,这只是在一般情形,例外的情形有两种:其一,构成不正当竞争;其二,某主体对该标识的使用足以使之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10]我国的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其特定性与明确性更是明显。
[1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12]前注3揭文,第172页。
[13]“公地灾难”的经典经济学模型见于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vol. 62, pp.124-142; Steven N.S. Cheung(张五常),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vol.13, pp.49-70.
[14]这是对商标权进行法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参见William Landes and Richard Posner, Trademark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7, vol. 30, pp.265-309.
[15]在此,我们借用了经典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享益财产的各个主体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也就是说他们面临同样的技术条件,因此具有相同的产能与成本,See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vol. 62, pp.124-142; Steven N.S. Cheung(张五常),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0, vol.13, pp.49-70.
[16]当然,培育商标不仅仅需要做宣传,更需要改进产品质量,而这一切都要耗费成本,在此,为论证之方便,我们以用于宣传的人工费指代所有此类成本。
[17]此表系依据Terry Anderson & Fred McChesney ed., Property Rights: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4, Table II.2修改而成。
[18]在某标识进入“专有”领域(即获得商标注册)之前,由于任何进入该行业的经营者均可以使用该标识,因而,为使顾客能够购买自己所生产的标注这一标识的商品或服务,每个经营者都必须支付一定的宣传成本,否则,顾客无法知道哪个经营者提供了标注该标识的商品或服务。
[19]“公地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进入者对已经在公地之中者产生的负外部性——即后续的进入会降低所有在先进入者的收益。
[20]如果我们仍旧坚持每家企业只能雇到1名宣传员的假设,那么,若不考虑交易成本,则拥有商标权的企业可以授权另外3家企业使用其商标,而授权使用费的总数最高可达60元((85-65)×3),再加上其自身使用商标的获益20元,其总收益仍为80元。
[21]这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申请注册的成本足够低,而事实上,实务中也的确如此。
[22]需要注意的是,如上面的例子所示,如果使用某一商标的每家企业都生产相同质量的产品,那么,商业标识能够减少信息搜寻成本的这一特性,并不因为其本身是否能成为注册商标而有所改变——只要它足以促进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也就是说,即使“共用名称”不能依法获得注册,该标识仍然可以产生正的价值。另外,“共用名称”为多家企业所共同使用的局面,还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如果某些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以图搭注重长远利益的优质企业的便车。很显然,这也是“共用名称”可能造成效率损失的一个原因,而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是在一定条件下减少此种效率损失的措施。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具体展开。
[23]参见前注3揭文,第180页。
[24]参见前注3揭文,第179页。
[25]此时,共有5名宣传员,由上表第(6)栏可知商标的净价值为75元,而乙投入3名宣传员,故其将取得商标净价值的3/5,也就是45元。
[26]此时,共有6名宣传员,由上表第(6)栏可知商标的净价值为60元,甲、乙投入3名宣传员,故将均分此净价值,也就是各获30元。
[27]这实际上是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也是古诺双寡头竞争模型(Cournot duopoly)),而博弈双方各投入3名宣传员是此模型的古诺-纳什均衡点。在这样一个对称的静态博弈模型中(也就是双方需要同时作出策略选择),甲、乙都会进行如下推理:假如对方遵守约定雇佣2名宣传员,则我雇佣3名就比雇佣两名能获得更多收益;假如对方违反约定雇佣3名宣传员,则我雇佣3名也不会比雇佣2名少得收益,因此,无论如何我应当雇佣3名(雇佣3名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弱的支配性策略(weakly dominant strategy))。注意:无论对方选择雇佣2名还是3名宣传员,对甲、乙双方而言,选择雇佣3名以上的宣传员始终比选择雇佣3名的收益为少。有关于此的一个简单线性模型,可参见James Buchanan & Yong Yoon, Symmetric Tragedies: Commons and Anticommons, 4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8-9 (2000)。
[28]在此我们没有考虑维护商标权的成本问题。法经济学理论认为:与单个主体的私有相比,共同所有可能降低维护权利的成本,这是因为每一权利主体维护其权利的边际成本递增之故。例如,一家企业需要投入500元才能监控50%的商标盗用情况,而两家企业可能只需要各负担200元(总共400元)就可以监控50%的商标盗用情况。参见Dean Lueck, Common Property as an Egalitarian Share Contrac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5 (1994), pp.93-108。不过,,是否足以抵消共有产权导致的租金耗散,还有赖于对具体事例进行经验性的研究。
[29]参见前注3揭文,第180页。
[30]See Lloyd Schuhfabrik Meyer Gmbh v. Klijsen Handel BV, case V-342/97[1999], ETMR690, 699.
[31]所以,商标被认为是一种关系,是标识与商品或服务之间特定的、指示性的符号关系。See Barton Beebe, The Semiotic Analysis of Trademark Law, 51 UCLA L. Rev. 621, 2004, p648.
[32]Jeremy Phillips, Trade Mark Law: A Practical Anat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9.
[33]“获得显著性”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描述性的丧失(实际上也不可能),而只是显著性超过了描述性。参见[美]米勒、戴维斯:《知识产权法》(英文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4]See William Landes and Richard Posner, Trademark Law: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0, 1987, pp.273-274.
[35]同上注揭文,pp.291-292.
[36]在此,。不过,即便放松这一假定,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此种成本的信息也会增加,从而改进人们对它的估计。
[37]在此,与通常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我们假设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或恒定)。
[38]如果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此处所谓“授权的最佳时机已被延误”,也就是指,由于有太多的主体投入使用“共用名称”,导致其因使用而产生的显著性又丧失了。
[39]参见前注3揭文,第173页。
[40]在前注3揭文中,作者并不赞成“强者通吃”的结果,但其认为是2001年商标法第11条第2款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他认为,该条款的适用是在肯定“强者通吃”。本文此处正是质疑这一点,提出商标法的这一规定并不是采用“强者通吃”的标准。
[41]对于实务部门操作流程的介绍,是为了回答有些人可能会提出的两个质疑:其一,如果在先的申请并不具有显著性,而在后的申请才具有之,在先申请者显然不能获胜;其二,如果在先的申请是抢注他人的未注册商标,其是否能成功呢?此处所述之商标局关于商标注册的操作过程,笔者是通过详细咨询实务人员而得到的有关情况,特此表示感谢。当然,一如成例,文责由笔者承担。
[42]参见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页。
[43]曾陈明汝:《商标法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44]See Windsurfing Chiemsee Produktions- und Vertriebs GmbH v. Boots- und Segelzubehör Walter Huber and Franz Attenberger, Joined Cases C-108 and 109/97 [1999] ETMR 585.
[45]J. Thomas McCarthy, Trade Mark Law: A Practical Anat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9.
[46]参见TRIPS第15条第1项之规定。
[47]See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4th at Thomson West, 2001, pp.15-46; Robert P. Mergers, Peter S. Menell &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657.
[48]See “Coca-Cola Co. v. Koke Co. of America et al.”, 235 F. 408; 1916 U.S. Dist. LEXIS 1380.
[49]690 F. 2d 786, 5th Cir. 1983.
[50]在该案中,原告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其中一份是对新奥尔良地区100名女士(她们每月使用本案涉及的那一类商品至少3次以上)的调查,另一份是在新奥尔良地区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所作的调查。依据调查报告以及实际使用和广告这些间接证据,。See Robert P. Mergers, Peter S. Menell &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658.
[51]423 F.2d 845, 1970 U.S. App. LEXIS 10392.
[52]596 F.2d 111, 1979 U.S. App. LEXIS 14469.
[53]531 F.2d 366, 1976 U.S. App. LEXIS 13064.
[54]See Aloe Crème Laboratories, Inc. v. Milsan, Inc., et al., 423 F.2d 845, at 850, 1970 U.S. App. LEXIS 10392.
[55]Robert P. Mergers, Peter S. Menell & Mark A. 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p.657-658.
[56]参见前注3揭文,第173页。
[57]的确,在诸“小肥羊”商标案中,,但并不代表这样的司法操作是正确无疑的,显然,他们并未真正掌握确立“第二含义”理论的目的究竟为何,也不了解前述美国多年来的司法经验,结果造成了“共用名称”注册为商标系“强者通吃”这一不被广为接受的结果,而实际上,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本不应该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被如此操作。
[58]即使某一企业在同业竞争者中并不具有明显的业绩优势,或者本行业中的确另有“龙头老大”存在,这也不妨碍该企业通过长期使用“共用名称”而使之产生第二含义,只要消费者能获得产品出处的信息即为已足。
[59]参见前注3揭文,第178页。
[60]参见前注3揭文,第179页。
[61]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应然、而非实然状态,因为其中还涉及企业、法官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实际上,笔者对内蒙古小肥羊公司获得商标注册后反过头来打击其他使用“小肥羊”商标的竞争者并最终胜诉的判决是持否定看法的,法官无视“在先使用权制度”而判给了内蒙古小肥羊公司以独占地位是不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依据这样的判决就认为“相关企业会积极投身于注册‘共用名称’的争夺之中、从而导致过度投资”,以及“强者可以通吃”,是不能成立的。本文这一部分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而进行论述的。
[62]参见前注3揭文,第182页。
[63]同上注。
[64]同上注55揭书, p654.
[65]该案请参见孔祥俊、武建英、刘泽宇:《WIO规则与中国知识产权法——原理·规则·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66]单纯“小肥羊”这三个字的中文文字商标,内蒙古小肥羊公司的公告期刚刚于2009年9月14日才届满。
[67]参见前注3揭文,第178页。
[68]参见前注3揭文,第176页。
[69]如前所述,在商标审查的实践中,对标识的审查主要就是商标检索,即看看申请的标识是否与在先的商标相同或相似,所以,审查员不会、也无法去追究申请的标识是否会侵权他人的在先权利,因为这个范围实在太大,要求审查员主动审查,只会降低审查效率。在先权利的主张,完全依赖于权利人的自行主张。这就给了申请人与在先权利人进行磋商的空间,以使得商标注册能获得通过。
[70]See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4th ed.), Addison-Wesley, 2003, pp.78-80.
[71]同上注揭书,p93.
[72]“反公地灾难”这一概念最初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Heller基于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权配置之考察而提出(See Michael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1, p.621. ),最近,Heller教授又在其专著The Gridlock Economy (Basic Books, 2008)中对此理论进行了全面展开。不过,对于“反公地灾难”究竟是否与“公地灾难”有实质区别的另一种产权形态,还是“开放地”的一种表现形态,法经济学界似乎尚无定论。如本文所示,“反公地灾难”也可能是公地灾难的一种诱因,并且,其与“敲竹杠”(holdout)引发的交易成本问题也不无相似之处(参见Dean Lueck and Thomas Miceli, Property Law, in A. 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 ed.,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Elsevier (2007), pp.193, 238)。
[73]关于这一点,与前文所介绍的我国商标申请、审查的实际操作也是相吻合的。
[74]参见前注3揭文,第184页。
[75]参见前注3揭文,第186页。该文还提到,,但又认为此项条件非其文章主题所涉,因而未作展开,为此,我们也不准备深入讨论“公共利益”问题。
[76]有关征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参见Dean Lueck and Thomas Miceli, Property Law, in A. 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 ed.,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Elsevier, 2007, pp. 238-242.
[77]参见前注3揭文,第178页。
[78]当然,假如由共有财产向私有财产转换,则可能出现这种“适应成本”问题。不过,即便如此,要确定这种成本的大小以便给予补偿同样需要耗费成本,因此,补偿仍可能不是一种最有效率的规则。
[79]参见前注3揭文,第179页
最新资讯
-
08-25 1
-
地方商标战略及其制度完善——以《湖北省著名商标认定与促进条例》的制定为例
08-31 2
-
08-19 1
-
知识产权战略视角下的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之路——以山东省枣庄市为例
08-29 0
-
05-20 0
-
08-2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