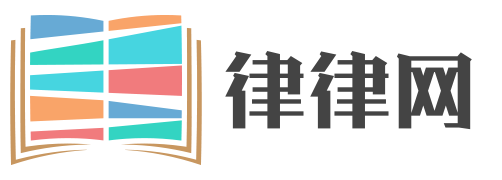孙某合同诈骗案辩护词
发布时间:2019-08-02 23:53:1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和吉林车宏伟律师事务所受孙某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孙某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们作为孙某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在本案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就参与了案件的进程,为孙某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多次会见孙某,做了一定的调查,曾就本案的相关问题向检察机关提出过一些意见,进入审判阶段以后,我们又阅读了全部案卷材料。结合几天的庭审情况,现就公诉机关指控孙某的几项犯罪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认真考虑。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孙某犯有行贿罪、挪用资金罪、虚假出资罪和合同诈骗罪均不成立,应依法宣告孙某无罪。
一、关于行贿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孙某在与A石油公司合作成立B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以后的项目运作过程中,先后四次给付A石油公司国际部经理仇某钱款共计港币19.90万元,仇某为孙某与A石油公司合作成立B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以后的项目运作上提供了帮助,据此公诉机关认为孙某犯有行贿罪。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此项指控不能成立,指控孙某犯有该项罪名依据严重不足。实际上该项指控完全是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对仇某的判决为根据得出孙某行贿的结论,进而认定孙某犯有行贿罪。辩护人认为,,即使仇某真的犯有此罪,也不能当然得出孙某行贿的结论。我国刑法规定的行贿罪是指行为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所以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就成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本案中有如下一些事实和情节值得法庭关注:
第一,B能源公司是合法成立的公司,对此应该不存在任何异议,仇某是B能源公司的董事之一也应该没有任何异议。既然是董事,其赚取董事的报酬也属理所应当。
第二 ,孙某支付给仇某的这几笔款是董事费,该费用的性质应该得到法庭的认定。不但孙某多次强调这些费用是董事费,仇某也曾在2006年6月1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讯问笔录(卷宗23页)中承认这些费用都是董事费,虽然朱某甄否认听说过仇某领取董事费的事,但他只是表示“没有听说过”,不能否认发放董事费的事实;裴某欣证明发董事费应该披露,但“没有披露”同样不能说明就没有发过董事费,也不能说明没有披露而发放的就不是董事费,何况当时的B公司为非上市公司,对董事费事项无需披露。
第三,B能源公司和B集团公司的所有董事都领取过董事费(包括朱某甄、于某光、吴某杰等人),这些董事费的发放采取的形式与仇某领取的董事费的形式是完全一样的,既没有董事会的决议,也没有公告披露,给仇支付董事费完全是阳光下的公开作业,孙某没有做任何隐瞒。以同样形式领取同样性质的款项,给朱某甄董事费不构成行贿,为什么给仇某就构成了行贿?
第四,本案发生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有其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 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付出劳动而没有报酬的情形(慈善和自愿行动除外),既为公司董事,收取董事费当然合情合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几笔款项的性质。
第五,孙某支付这几笔款项的目的是正当合理的,不存在非正当性或非法性。按照孙某的说法,给仇某支付董事费是让他有动力办好B公司,使与A公司的合作顺利进行,不能中途停止合作;按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号判决书的说法,是“能对其同A公司更好的合作提供方便”,仇某利用职务便利,“为B公司的成立及其项目运作提供帮助”。以上这些说法能得出“不正当”的结论吗?B公司是正当成立的,就算仇提供过帮助,有何种理由能认定提供帮助就是非法或不正当呢?孙某与A公司的合作也是正当的,意图不能中途停止合作也是正当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论也只认定仇某“为他人谋取利益”,却没有认定“为他人谋取非法或不正当利益”,这不是简单的字面疏忽,而是极其清楚地说明孙某为仇某支付款项的正当性。既是正当的目的,何谈行贿?既目的正当,又怎能构成行贿犯罪?
第六,有一个重要情节请法庭注意,公诉机关指控孙某犯行贿罪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孙某要仇某在B公司成立问题上给以帮助,且不论这一要求是否正当,在时间问题上也存在重大误区。B公司成立于1998年9-10月,而向仇某支付董事费的时间却是2000年1月至2000年4月,此时,公司早已成立且正常运行,还需要向仇“行贿”求其帮助“成立公司”吗?
第七,仇某的身份是A公司的国际部经理,在A公司内部属中层干部,对公司海外投资或成立合资企业这类重大事项究竟有多大权力不必多论,众所周知。事实上,在决定合作问题上,决策权的行使根本轮不到仇某这类人物。如果为达到某些非法目的而向A公司某些成员行贿,相信孙某这类人士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仇某在孙某与A公司合作上只起到考察和汇报作用。仇某进行了考察是真切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孙某向仇掩盖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事实,X公司客观存在,运转正常,也没有证据表明后来的付董事费与先前的仇某汇报有什么反向的必然因果联系。
第八,行贿罪侵犯的客体既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也有国家经济管理的正常活动。孙某支付仇某董事费的行为,其结果没有损害国家经济管理的任何活动,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标准是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孙某的行为既不存在任何社会危害,认定其有罪当无任何依据。至于仇某做为A公司的工作人员应该不应该收取海外公司的董事费用,应由A公司自行决定,另行判断,不能因为仇某不该收取款项而反推孙某构成行贿罪,这是一种客观归罪行为,历来为我国刑法理论所反对。
除以上几点外,还有两点值得法庭考虑的问题,其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办理仇某案件时,曾讯问过孙某,明确表示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正因为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并没有对所谓孙某行贿一事并案处理,也没有对行贿案移送长春一并检控。其二,本案发生在香港,孙某本人为港商,在案件管辖上也值得研究,,对涉及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尤须考虑。对上述两个问题虽然不涉及案件实体的处理,但值得法庭在做出判决时认真研究。
最新资讯
-
08-25 0
-
08-24 1
-
08-14 0
-
06-23 1
-
09-12 0
-
08-2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