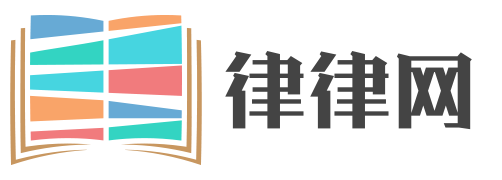合伙债务、习惯法与国家的介绍之上海商界习惯与大理院解释
发布时间:2021-05-09 18:15:15
合伙债务、习惯法与国家的介绍之上海商界习惯与大理院解释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迅速发展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经贸中心,各式各样的盈利性企业大量涌现。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限公司还是个崭新的事物,规范它的法律也极为稀少[3];上海滩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合伙制”企业[4]。对于合伙企业债务的分配,上海商界的“历来通例”是:“合伙组织大率先订议据,载明每人所占股数,盈则按股均分,亏则按股分担,将来对外债务即以此议据为标准”;如果合伙成员中有一人或数人“资力不足”,其他合伙人只“担认自己所持有之股份而止;不足之数,则由债务人与债权人磋商折扣了结”[5]。
但是,这一习惯遭到了大理院的否定,它作出的判例认为,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不能以内部分配协议对抗债权人。在上海商界人士看来,大理院的这种判例,对上海商业打击非常大:“维护经济之进步,必先使投资者无意外之损失。如果一经占有若干股份,而日后因其他合伙员之牵涉,几举全部财产以殉之,权衡利害,谁不裹足?!”;“公众对于合伙营业势必视为畏途,谁复有意经营?!”;“商业方面,所受打击,当非细微”。除此之外,上海商界人士还拿合伙与有限公司作比较,为其习惯辩护。他们认为,有限公司也是持股者以自己持股为限承担有限债务,但“未闻阻碍经济之进步”;并且,上海商界的这种习惯,与有限公司相比,更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合伙员是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去还债,而有限公司持股者只是以自己所持的股份去清偿[6]。鉴于以上这些理由,,请求大理院作出解释,承认上海商界习惯法的效力。
国家与习惯法的较量正式开始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这时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以强迫社会遵从它的号令。表面上,国家拥有强大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而上海总商会不过是一区区民间组织,对比之下,上海总商会似乎输定了,国家可以径直否定习惯的效力。但是,在那个时代,、软弱涣散的机构,上海甚至不在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7]。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的上海总商会是个能量巨大的组织,作出过不少叱诧风云的举动,在全国的商界、政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8]。大理院与上海总商会的这次冲突,没有体现在“力”的角逐上,而是表现为“理”的论证和说服上。上海总商会的请求,是借助“判例条理”而提出的。该商会首先援引民国二年上字第六十四号判例――该判例规定了“法律无明文者从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的规范,认为大理院关于合伙债务的判例所确认的规范属于“条理”[9];根据“法律无明文者从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大理院判例所确认的“条理”,其法律效力低于上海商界的“习惯”,因此,大理院必须服从上海商界的习惯法。除此之外,上海总商会还列举了上述种种维护该习惯的理由,以论证该习惯存在的价值。
接到上海商界的请求之后,民国十五年八月九日,大理院发布了名为“合伙员之责任与习惯”的法律解释。该解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铺陈了上海商界请求确认该习惯的种种理由,第二部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部分中,大理院对合伙的“公私”性质进行了界定:“盖以合伙为公同业务,合伙债务非单纯合伙员各人之债务可比”。接着,大理院由此推断:“(合伙债务)原应由合伙员公同负责,苟合伙员有不能清偿其应摊债务,即属合伙之损失。依公同分配损益之原则,自应责令他合伙成员代为分担”。最后,大理院还特别强调:“唯此项条理并无强行性质。如有特别习惯,而合伙与债权人又无反对该习惯之意思表示者,得依习惯办理”――这一点为习惯的适用留下一定的余地。但是,适用与否,还要取决于大理院:“至有无此种习惯,属于事实范围,。在这一解释中,大理院强调了合伙的“公同”性,间接地暗示了该习惯的“自私”,坚持了自己以前判决所提出的“条理”。
最新资讯
-
合伙债务清偿问题研究情况之合伙财产和合伙人个人财产清偿债务的顺序
05-14 1
-
08-13 1
-
11-21 0
-
08-27 0
-
08-31 1
-
08-1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