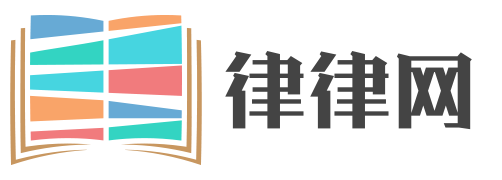衡平理念下的法人制度缺陷之救济
发布时间:2020-04-15 11:00:15
衡平理念下的法人制度缺陷之救济
——公司人格否认若干实务问题探析
公司法人制度之降生,似印证了罗马法的一句古老格言:“法之极、恶之极”(summum ius summa iniuria),其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在促进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亦充当了欺诈舞弊者的“护身符”,使得投资者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日益突出,产生了令人困扰的公司问题。为矫正制度上的偏差,回复价值目标的平衡,各国无不找寻新的法律措施,根植于衡平理念的公司人格否认理论遂应运而生并成为其中最突出者。在我国,现代法人制度确立的时间虽不长,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却很快出现且呈蔓延之势,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如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母子公司之间人员、财产、业务等严重混同;名为公司实为个人的独资企业;企业“脱壳”经营;公司“假破产、真逃债”等。于此,我国相关立法尚无有效之规制措施,审判实践中亦未形成系统、成熟的做法。近年来,公司人格否认问题虽引起我国法学界的重视,但迄今仍主要停留在理论研讨阶段。当前,已有债权人在诉讼中要求对公司采用公司人格否认,判令股东承担责任,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可操作的公司人格否认规则可谓迫在眉睫。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参酌国内外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与实践,在本文中对公司人格否认法理的若干实务问题作一探讨。
一、公司人格否认——司法实践中的界定
公司人格否认:涵义之澄清。
公司人格否认 [1] (disregard of corporate ersonality),又称作“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在德国亦被描述为“直索”(Durchgriff),意指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不承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而由公司股东对公司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措施。
公司之独立人格犹如在股东与公司外部关系人之间竖起的一道隔离墙,通常情况下,依法设立的公司其独立人格都应受到尊重而不被否认,法律亦不能透过公司这层“面纱”要求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出资额以外的责任。然,公司独立人格之维系须以公司“ 面纱”被用于合法目的为前提。若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以谋取私利,,将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视为一体,令股东“走上前台”,直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正如美国法官桑伯恩(Sanborn)所说:“公司在无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应被视为法人具有独立人格;但是如果公司的独立人格被用以破坏公共利益,使不法行为正当化,袒护欺诈或犯罪 ,法律即应将公司视为多数人之组合而已。” [2]
公司人格否认之滥觞,乃基于衡平(equity)之理念。衡平原则具有两层意义:一为缓和严格的法律;二为就个案通观相关情事,个别化地实现个别正义。由于法律具有一般普遍性,不能适应一切情事,在面对个别、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时其一般性将遇到困难,导致法律的适用与其价值相背离, ”(an obstinate and ignorant tyrant)。[3] 此刻即需藉助衡平加以调剂以弥补法律因其一般普遍性所生之不足。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正义具有一般化的性格,显现在抽象的规范,适用于同类案例的多数之人。衡平则是针对个案的特性,斟酌相关情事,而求其妥当。”[4]公司人格否认正是各国运用衡平原则通过个案否认的方式矫正公司人格独立制度不合目的性的产物。因此,公司人格否认虽然表现为无视公司独立人格,否认股东有限责任,但它并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永久的剥夺,仅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将公司形式上存在的法人人格视为实际上不存在。公司人格被否认,意味着“在某些情形下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被钻了一个孔;但对于被钻孔以外的所有其他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5]究其本质,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司法规制而非立法规制。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将公司人格否认与相关概念进行区分。
1.公司人格否认与法人否认说。法人否认说是传统法人理论中的一种学说,该学说不承认法人之存在,将法人还原为多数个人之集合,认为法人只是人们的主观臆断,其核心在于用自然人的人格代替法人组织的主体资格,不认可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而公司人格否认的建构是以坚持公司具有独立人格为基础的,没有公司人格独立,就不会产生公司人格否认。公司人格否认并不是对法人制度的否定,其精髓恰恰是为了维护法人制度的宗旨。因此,在公司是否具有独立人格的问题上,两者的立场截然相反。
2.公司人格否认与公司的强制解散或撤销。公司的强制解散或撤销,是依国家公权力使公司独立人格消灭的法律行为,各国公司法对此均有相应的规制措施,而不属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调整的范围。公司被强制解散或撤销,公司独立人格即遭永久、全面之剥夺,此行为具有对世的绝对效力,是对公司违背设置目的所作的根本性解决,这不同于公司人格否认仅有个案效力。此外,公司解散或撤销后所进行的清算仅以公司自有财产为基础,终结公司现存法律关系,债权人不能以此为由向股东追偿公司债务,这与公司人格否认以追究股东责任为出发点也大异其趣。因此,纵然公司已被强制解散,若存有否认公司人格之情事,当事人仍可主张否认公司人格。二者独立发挥作用,并行不悖。
否认瑕疵公司人格之诉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与衡平。
瑕疵公司,系指形式上已经获准注册但实质上并未满足公司设立要件的公司。瑕疵公司之瑕疵表现为股东瑕疵、资本瑕疵及章程瑕疵。通过诉讼对瑕疵公司设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由瑕疵制造者承担责任,即为否认瑕疵公司人格之诉。在我国,对于瑕疵公司的处理属于工商行政机关的权限,如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条即规定了对瑕疵公司的行政处罚措施,。但在实践中,并不排斥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公司设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如此一来势必引起司法权与行政权产生冲突,如何处理?笔者以为,我国公司法是部门立法的产物,行政干涉色彩过于浓厚。从“司法最终解决”的法治原则来讲,。今后修改公司法时,,并构建公司设立无效的诉讼法律模式和瑕疵责任制造者的民事责任制度,以诉讼制度模式取代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行政处罚措施。这样可确保司法权的公正干预,避免行政权滥用,维护市场主体的稳定。而目前,,应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建议工商行政机关吊销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如果工商行政机关拒绝吊销的,。
需强调的是,虽然否认瑕疵公司人格之诉与公司人格否认在基本做法上十分相似,皆以诉讼方式认定公司不具有法人人格,但前者旨在自始否认公司人格,其结果是引起公司的解散或撤销,并对公司进行清算,后者则仅具有个案意义;否认瑕疵公司的人格,并不当然地排斥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适用,而公司人格否认的目的则在于追索股东的无 限连带责任。故对两者不可等而视之。
,可谓学界研究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时探讨最多的司法解释文件。《批复》针对出资人虚假出资问题区分了两种情况予以处理:(1)出资不足的情况下,若达到了法定的最低资本额,出资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对法人债务承担责任。此为出资人基于公司法对股东出资义务的规定所承担的资本填充责任,并非基于公司人格否认产生的无限连带责任。(2)在出资人未出资或出资未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情况下,应认定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由出资人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对于此种情形,有学者认为是“区别地否认法人格”,[6]有学者认为“它类似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但不是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7]笔者以为,这一情形实际是《批复》运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去处理本应通过否认瑕疵公司人格之诉解决的问题,以致实践中既要在判决理由中认定公司不具备法人人格,却又不裁令解散公司,且公司尚未清算既判令全体股东 承担无限责任,在法理上显然有欠严谨。
二、公司人格否认——可资适用的主要情形
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虽发轫于上世纪初,然迄今仍主要以判例法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统一的理论,有关该法理适用的全部问题“仍被包裹于比喻的迷雾中”。[8]因此,该法理的适用情形也无统一的标准可循。在其肇始地——美国,公司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一般有五种经类型化的案例:(1)欺诈(fraud);(2)不遵守公司的形式(absence of formalities);(3)资本不足(undercapitalization);(4)资产混合(commingling of assets);(5)控制(control)。[9] 在日本,根据其判例解释,该法理适于两种情形:一为滥用事件;二为形骸事件。 [10]依笔者愚见,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千变万化,不可能穷尽,公司人格否认作为一种司法规制手段,其运用也主要依赖法官对公平正义理念的体恤理解,概括适用情形之目的在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参酌国外做法,结合 司法实务,笔者对公司人格否认在我国适用的情形做如下分析。
资产显著不足。
资产显著不足,意指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事业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足时,可判令股东承担责任。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的“血液”,是公司信用的基础和公司债务的总担保。公司资产不足可能损害与之交易的第三人的利益,或将对方置于极不利的地位,显属不公,故此种情形也应否认公司之人格。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有最低资本额的规定,但公司资产是否显著不足并不以法定的最低资本额来衡量,而以公司的营业状况、交易的性质为标准。例如,以少额资本成立的公司经营高度危险事业,即便公司的资本超出法定最低资本额,也应认定公司资产不足。通常情况下,认定资产不足以特定法律关系成立时为计算标准,若某法律关系成立时,公司资产充足,但因其后蒙受了正常的经济损失,则不应作为资产不足处理。至于实践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出资人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问题,应通过追究出资人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或提起否认瑕疵公司人格之诉加以解决,无须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当前则可依据《批复》的精神处理。
关联法人间的过度控制。
关联法人,以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为典型和突出,而过度控制(excess control)的情形也主要集中在母子公司之间。母公司和子公司在法律上是各自独立的法人,能够分别承担独立的责任。母公司基于其特殊地位,对子公司的经营决策形成影响是必然的,此亦为法律所允许。然若此种控制超过必要的限度,则母公司即应当对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母公司对子公司过度控制的表现形式通常有:母公司拥有子公司的全部股份;子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由母公司的董事或高级职员兼任;子公司的流动资本和营业费用主要靠母公司临时垫付而不是长期投资;母公司与子公司用相同的名称营业以及子公司资产不足以偿还公司债务等。对过度控制这一情形,母公司责任的成立基本上要求符合下列三项要件:第一,母公司对子公司须具有支配性的控制(dominating control);第二,母公司因行使控制力而为诈欺或不诚实行为(use of control to commit fraud or wrong);第三,债权人的损害与母公司的行使控制力,须具有相当因 果关系(proximate directors)。[11]值得注意的是,:“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则由控股企业承担。”该规定的做法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过度控制的理论。,可以参考国外对过度控制案件处理的方法来认定控 股企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当然,若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已达到相当程度而致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人格发生混同 时,则可依公司人格混同的理论否认子公司之人格。
另外,关联法人之间还存在大量的资金相互调用、流动和借贷的联系。此种联系所衍生的问题是:当子公司破产或重整时,母公司对子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以何种顺序受偿?是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还是次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受偿?抑或根本不承认母公司对子公司之债权?倘若一概将母公司对子公司享有的债权视同其他债权人对子公司的债权,则很可能造成不公平。对此, 创立的深石原则(Deep Rock Doctrine),即指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存在令子公司资产显著不足、对子公司控制权的行使违反受任人的诚信义务、无视子公司独立人格而违反公司法的规范性规定、资产混同或不当流动等不公正行为,在子公司破产或重整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应后于其他债权人对子公司的债权受偿。若无上述行为,则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权应与其他债权人对子公司的债权平等受偿。由于在确定母公司债权的受偿顺序时需预先对母公司的行为进行考量,故该原则又称为“衡平居次”(equitable subordination)法则。我国台湾地区1992年修改“公司法”时,也曾借鉴深石原则拟新增如下条文:“第三百六十九条之七控制公司直接或间接使从属公司为不合营业常规或其他不利益之经营者,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之债权,在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应负担之损害赔偿限度内,不得主张抵消,无论其有无别除权或优先权,于从属公司依破产法之规定为破产或和解,或依本法之规定为重整或特别清算时,应次于从属公司之其他债权受清偿。”[12]
公司人格混同。
公司人格混同亦称为公司人格形骸化,系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合,令公司人格仅具象征意义,公司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而成为股东的代理或工具,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情况。在一人公司和母子公司的场合下,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况较为严重。公司人格混同包括组织机构的混同、财产的混同以及业务的混同,三者任居其一即构成公司人格混同。我国实践中公司人格混同的典型体现有:某些企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名为公司实为个人;同一资产设立几个公司;一个股东承包或租赁公司,其他股东则只参与分红,不参与经营和管理等。在审判实务中,已有公司人格混同理论适用的案例。例如,在贵州省升平建设发展总公司诉贵州省大众房地产开发公司、贵州省房地产开发联合公司债务纠纷案中,,判决被告大众公司应对被 告联合公司偿还原告200万元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
法律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股东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不仅表明该行为本身具有主观故意和欺诈性,而且使社会整体利益的调整难以实现,违背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故对此行为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由股东承担规避法律的责任。股东利用公司形态规避法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为规避法定的竞业禁止义务而成立公司;假装解散以规避劳动法上的禁止性规定;通过设立公司以规避禁止取得自己股份的规定;为享受某国或某地的特殊政策而在该国或该地成立公司,实际并不在那里开展业务;虚设股东以规避关于股东人数的规定或便于享受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等。
利用公司形态逃避合同义务或债务。
此为我国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滥用公司人格问题。如一些公司成立后,股东即将投入公司的法律上所必须的资金转移、抽逃,而后向银行大量举债,攫取国家资金,待债权人事后发觉并追究时,始知公司一无所有,此际债权人却因无法追偿幕后股东而束手无策,幕后股东则中饱私囊,逍遥法外,公司虽已入不敷出,但股东个人却越来越富有,名之曰“金蝉脱壳”;一些企业在经营陷入困境后,以改制、重组等为名,将债务留在原企业,而以原企业的原班人马及主要资产设立新企业,即企业“脱壳”经营,令债权人只能对新企业的财产望而兴叹,名之曰“轻装突围”;一些企业为逃避巨额债务先宣告破产,再以原有的营业场所、原有人员设立另一公司,且经营业务与目的与破产企业完全相同,名之曰“死而复生”。在我国“诸侯经济”的氛围下,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又因得到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的支持而愈演愈烈,非以公司人格否认无法制止。此外,为回避合同中规定的不作为义务如竞业禁止、保密等而设立公司也是表现形式之一。:“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该规定意在借鉴公司人格否认理论以遏制企业利用改制恶意逃债的行为,对从立法上确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一次有 益的尝试。不过,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优质资产尚待摸索。
若股东为使公司逃避债务,操纵公司怠于主张到期债权或放弃享有的债权,或将公司资产无偿或低价转让,则公司的债权人可通过行使合同法上的代位权和撤销权获得救济 ,这不涉及公司人格否认的问题。
利用公司形态回避不法行为责任或分散危险。
在公司存在违法或侵权行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或经营高风险事业时,常发生此类情况。例如,成立公司从事不法行为以逃避可能承担的民事或刑事责任;为回避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或为回避对旧公司从业人员的加害行为所生之雇主责任而解散旧公司,设立在组织、营业内容上与之完全相同的新公司;由于企业风险较高而预先分立公司以图分散赔偿责任等。此时,为保护受害人或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应当适用公 司人格否认制度。
两种情形下应排除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1)股东不得为自己的利益主张公司人格的否认。股东一旦依自己的意志选择以公司形态经营事业,则必须承受公司作为法律上之独立主体而带来的法律后果——公司人格独立带来的利益和滥用公司人格带来的负担。基于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利益与负担应当是统一的,股东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亦应承受随之而来的负担。若允许股东为自己的利益而主张公司人格的否认,则无异于纵容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此原则已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2)合同对方违约在先。在合同对方当事人先行违约的情形下,特定当事人为避免对方先行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而规避合同义务的行为不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这是因为,特定当事人之所以利用法人人格规避本应承担的合同义务,乃是基于对方先违约的合法的自我救济,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将使特定当事人无法获得有效保护,使其利益受到更大损失。[13]
三、公司人格否认——对国家股东的适用
如何规范国有公司,特别是国有独资公司中国家股东的行为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无疑,为平等保护各种性质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必要时,也应对国家股东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直索其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尚有诸多问题需要研讨。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单就理论而言,国家作为一个特殊法人,自己不能行使股权,需委托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等中介组织代理其行使股权。若产生纠纷,以中介组织为被告,在程序上虽无障碍,但问题是:中介组织只是国家股东的代理人,依民法理论,代理人超越代理权而致他人受到损害,被代理人不承担责任,即是说,若中介组织滥用股东控制权损害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可能无法追索到国家股东。那么在追索国家股东责任的案件中,民法的代理理论是否当然适用?况且,中介组织多不是营利性组织,其又以何财产来承担滥用控制权所生之民事责任?,有人戏称其为“婆婆加老板”,。有学者主张可准用国家赔偿法追索国家股东责任,然国家赔偿法只适用于行政及刑事赔偿,用于民事赔偿略显牵强。其实,由于公司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在修订公司法时增设有关国家股东责任的条款,可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并由其以国库资产承担民事 责任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四、公司人格否认——诉讼程序中的诸问题
诉讼当事人的列明。
一般来讲,原告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无外乎三种方式:1.以公司及其背后的股东或新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2.由于公司已不存在,抑或认为起诉公司没有实际意义而仅以公司背后的股东或新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3.最初只起诉了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再追加公司背后的股东或新公司为当事人并变更诉讼请求。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为保持司法中立,法官原则上都不应主动追加股东或新公司为当事人。但是,在两种情况下法官可依职权直接追加股东或新公司为当事人并对其下达判决;1.依据查明的事实可认定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或者新旧两个公司无论名称还是实质皆为完全相同;2.股东滥用 公司人格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有时对当事人诉讼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依通说,举证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可以转移,后者则不能转移。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指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当案件裁判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由于不能举证或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所承担的败诉风险,故又称作证明责任。谈及举证责任的分配,既指对行为责任的分配,也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准则有四:1.实现实体法的宗旨;2.使裁判最大限度接近真实;3.程序公正;4.诉讼经济。[14]在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中,首先需证明原告与涉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何种债权债务关系,对此只需依照有关实体法及程序法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可,笔者不再赘言。值得研究的是如何证明被告符合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要件,在这一点上,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显然极不对等。因为涉及公司及其股东行为的各种账册、凭证、记录、文件资料等证据材料几乎完全掌握在被告手中,若坚持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则近乎褫夺原告之胜诉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将形同虚设,解决公司问题的初衷也将付诸东流。然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又可能导致债权人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危及公司法人制度的安定,。如何摆脱此两难境地?笔者认为,应当考虑采用表见证明的证明规则。所谓表见证明,亦即利用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中推定待证事实。运用此规则的具体要求为: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公司的登记状况及自己遭受的损失,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证明程度为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而后,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至被告方,由被告提供证据最终证明自己与涉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正当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此规则所转移的只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仍由原告负担,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不当行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仍应判决原告败诉,这也是表见证明与举证责任倒置之区别所在。然,此规则之适用,亦不排除在特殊情形下,为更好地彰显公平与正义而采取原告负举证责任或举证 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
判决效力的扩张。
在某公司被认定符合公司人格否认要件而判决其控制股东承担责任后,其他对公司提起诉讼并胜诉的债权人能否直接根据这一判决要求控制股东承担责任或执行控制股东,即要求该控制股东受这一判决的既判力、执行力等效力的约束?此即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判决中,对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可否扩张有消极说和积极说两种学说。前者否认判决效力的扩张;后者则有限度地承认判决效力可以扩张。国内有学者认为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并不当然地及于控制股东,[15]实际是采消极说;也有学者主张应当谨慎地采用积极说。[16] 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人格否认法理尚处于萌芽阶段,从坚持个案否认、保证程序的明确与稳定以及避免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角度考虑 ,采用消极说更为妥当。
五、公司人格否认——在中国实现法律化的思考
至今,我国立法尚未确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改制规定》等司法解释及有关判例也只是与公司人格否认的做法近似,此项制度基本上还处于蒙沌状态,因此,在我国实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化已是紧迫之事。对于实现法律化的途径,学界多强调了充分适用公平诚信、禁止权利滥用和公序良俗等民商法基本原则,,而对于引入判例法制度则关注不够。其实,判例法制度不仅可就个案创设规则弥补制定法之不足,且有利于司法统一,亦体现出公司人格否认法理本性的回归,。此外,引入判例法制度亦不失为一项比较经济的举措,对现行法律体系几乎不会造成冲击。笔者对引入判例法制度的设想是:1.根据我国的传统,判例可不作为法律渊源,但应作为先例得到遵从;2.;3.,,;4.国外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判例若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形不冲突,,作为 审判的参考,其中体现出的基本法理可以直接采用。
注释:
[1]目前也有学者对公司人格否认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就语译的表达,还是就程序上的操作乃至实体上的性质而言,‘公司人格否认’的说法皆不贴切”(见虞政平著:《质疑“公司人格否认”之说》,。笔者认为,该文作者的观点只是对“公司人格否认”这一概念的理解角度不同,并未否定这项制度的存在。至于“公司人格否认”这一概念是否准确,笔者将另撰文予以探讨,在本文中仍援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概念。
[2]United States v.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it Co.,142 Fed 2d 247,255(C.C.E.D.Wis.1905).转引自蔡立东:“公司人格独立与人格否认”,载《商法基本问题研究》,徐卫东主编,法律出版社20 02年6月版,第13页。
[3] C.K.Allen,Law in the Making,p.422. 转引自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册,第24页。
[4]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册,第24页。
[5] 陈现杰:“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述评”,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3期,第81页。转引自王天鸿:《一人公司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78—279页。
[6]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64页。
[7]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59页。
[8] Berkey v.Third Avenue Ry.,244 N.Y.84,94,155N.E.58,61(1926).转引自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4页。
[9] 刘连煜:《公司法理论与判决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年12月版,第48页。
[10] [日]末永敏和:《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第15—16页。
[11] See Powell,Parent and Subsidiary Corporations,at 4—6,(1931);Clark,supra note 14,at 72;Blumberg,supra note 11 ,at 114.转引自刘连煜:《公司法理论与判决研究》,第48页。
[12] 刘连煜:《公司法理论与判决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91 —92页。
[13] 刘贵祥:“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与审判实务”,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9期,第15页。
[14] 李浩:“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哲学思考”,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1期。
[15] 刘贵祥:“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与审判实务”,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9期,第14页。
[16]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78页。
作者单位:
最新资讯
-
04-02 1
-
12-06 0
-
08-15 0
-
01-25 1
-
08-17 1
-
03-0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