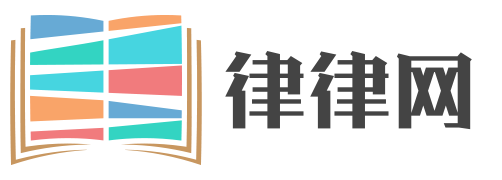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司法运用
发布时间:2019-08-19 23:25:15
[案情]
李某于1998年在某市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1999年5月将其出租给刘某,租期二年,2000年7月,由于该商品房所在地段房价猛涨,李某遂将该商品房出卖给陈某,谎称其亲戚在该房暂时居住,并办理了房产转移手续,。刘某得知此事,向李某提出,其为房产承租人,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李某应在出卖房产前三个月通知其本人。李某以时间紧迫,商机不可错失为由予以说明。,,保护其作为承租人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对案例的分析]
本案案情较为简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但在具体适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还在于以本案为例,对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利弊进行分析,进而就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完善提出个人看法。
一、本案中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利弊分析
不动产承租人在不动产动产出卖时,享有优先购买权,是各国立法通例,强化承租人的权利也是近代世界性的立法趋势,租赁权的强化又称之为租赁权的物权化过程。德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明确规定了租赁权的物权效力。日本的建筑物保护法和借地法也将承租人的权利与地上权一样加以保护,承租权和地上权统一被称为“借地权”,作为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34条、第104条、第107条、第124条,以及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15条,也分别规定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和基地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就不动产租赁权物权化以及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设定的立法宗旨来说,不外以下两点:
第一,维护已有的不动产占有与利用关系,避免土地所有与土地利用关系的分离,使已有的不动产利用关系得以延续,以最大限度发挥物的效用;
第二,一般而言,不动产的租赁对于承租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租赁权的物权化可以有效保护承租人的利益,使承租人不因不动产的出卖而遭不利。
就本案而言,承租人刘某如果以租赁的商品房作为当前的安身立命之所,此时在所有人出卖房屋时,刘某享有一定的物权性权利,对于维护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房屋通过市场交易很难取得的情况下,这种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无疑是承租人获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不可多得的途径。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在保护承租人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就本案而言,李某在商品房价格上涨以后,为抓住商机而出卖房屋,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出卖人在三个月前应通知承租人,那么出卖人至少应等待三个月之久,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出卖人坐失商机。
除此之外,我认为,传统立法对承租人赋予优先购买权的立法基础已一定程度上丧失了。
第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赋予的现实环境是不动产资源的匮乏,这一情况在当代得到了改变。在土地和房屋资源异常匮乏的情况下,立法追求的主要是生存和安全价值,是对一种基本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解决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一定程度了促进了这种基本价值的实现。但在现代社会,市场的高度发达,生活资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导致社会形成了一种以市场为媒介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效率成为立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对出租人而言,在不动产买卖关系中,如顾及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将可能因此支付巨大的机会成本。这显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效率机制的发挥。而对承租人而言,至少在房产市场里,这种优先购买权的赋予并不能起到保护其基本生活状况的作用,因为承租人也可以顺利从市场取得相应的房产。
第二,从维护既有的房屋利用关系而言,“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即可实现此目的。近现代各国基于对租赁权的保护,使租赁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在房屋易主后,租赁关系仍继续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既有房屋租赁关系的一种法律保护。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下,既使出租人将房屋出卖,承租人的租赁权仍然存在,并不受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房屋利用关系已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因此,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立法的第一个宗旨而言,租赁房屋的出卖并不会破坏房屋已有的租赁关系。况且租赁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基于合同而形成的债权关系,是有期限的权利。进一步而言,如果优先购买权的赋予是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者是一种稳定的预期的话,那么对于承租人而言,承租期限的维护是其主要目的,至于最后是否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并未包含在其预期之内。所以,从维护房屋利用关系而言,优先购买权并不能对此有实质性的贡献,“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即可实现此目的。
第三,即使在理论上认为,赋予承租人购买权终究可以为承租人在租赁期满后继续利用房屋,但由此支付的成本是巨大的。姑且不说承租人一旦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是否还能象在承租期间那样利用房屋,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仅仅从交易安全、公平角度进行利益衡量,结论就非常明显。
近代“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确立是传统民事法律关系规则体系的变奏,在这种规则约束下,租赁物的买卖被人为添加了“租赁关系”这一负担,正是由于这种负担的存在,才使承租人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出租人在出卖房屋时,由于受这种租赁关系的制约,本身已承受一种不利的后果。在一个不动产交易不发达的社会里,对买卖双方增加这一负担,在社会上获得了承租人的预期利益得到保护这一有利结果。但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使交易的快捷、安全至为重要。与此相对应,在一个动态社会中,不动产资源的效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不动产的买卖也不再局限于决策时间长、机会偶然的民事行为,而是表现为带有赢利色彩浓厚的商业行为。在快捷的不动产流动市场中,所有权的交易是受市场控制的,交易双方形式上的公平甚于以往任何时候。这就要求所有权人在处分所有权时,应直接依据市场来决策,不能过多地受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立法上保留“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几乎已达市场所允许的所有人承受负担的阈限,如果还要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则其代价必然是诸多市场交易的无法达成。此时,所损失的就不仅是出卖人可以获得的利益,而是整个市场的安全和效率。
就本案而言,承租人刘某在租赁商品房时,其目的是为了在二年期限内有效地占有和使用该商品房,对于是否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并没有稳定的预期。对于刘某来讲,在承租期内能稳定地占有和利用租赁物,是其现实的利益,法律当然应予维护,但在取得所有权这一问题上,所有权的取得与其租赁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优先购买权的赋予也只是给予承租人优先获得该商品房的所有权而已,这一优先权并没有实质的价值。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关系中,承租人想真正获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只是一种可能而已,租赁关系与买卖关系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如果在立法上想当然地予以确认,那么在保护一种虚幻利益的同时,损失的是众多第三人可能享有的机会和效益。比如,如果本案中承租人是外地打工人员,而买方陈某是房主李某的邻居,那么可以发现,即使留给刘某三个月的考虑时间,刘某也不大可能在此定居,即使其有能力购买房屋,也可在市场顺利获得。而陈某获得这一商品房却可以充分发挥该房屋的区位优势,这正是市场交易所欲达成的效果。但出卖人李某如果在决策时,顾及刘某的优先购买权,那么极有可能错过时机,使一个对双方极为有利的交易无法达成。
所以,应当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在立法上值得慎重考虑和谨慎选择。
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与共有关系中优先购买权合理性的比较
综观各国立法,在优先购买权的设计上,不外乎三种优先购买权: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和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在优先购买权的立法基础上,却颇不相同,限于篇幅,在于仅比较承租人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几乎是各国民事立法都加以明确规定的。设立此优先购买权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有利于稳定共有关系,维护财产秩序,减少共有人之间的纠纷。第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促进对物的有效率的利用。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共有人优先承购权,旨在防止土地的细分,并兼及消除共有关系,以尽地利。”也就是说,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不但能有效地促进物的利用效率,还能减少原共有人与可能存在的新共有人之间的纠纷。尤其对不动产共有而言,这一点甚为重要。在我国古代,为了促进不动产的有效利用,从北魏时就开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亲邻优先权。唐朝充分继承了此制度,如《唐律》规定,房地产买卖必须先问近亲,次问四邻,近亲四邻不要,才得卖与别人。与共有人的优先权同出一辙,亲邻优先权也是为了充分发挥不动产之经济效益,免除日后可能滋生的斗讼争端,节约社会成本。
由此可见,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的法定化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物的占有和利用秩序的问题,其所获得的社会效益是较大的。当然,从消极影响方面考虑,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以限制共有人的处分权,第三人在同等条件下丧失购买机会为代价的。但必须说明的是,优先购买权的赋予本就是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利益权衡的结果,是对纯粹市场规则的干预,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积极影响相比,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显属次要。
但对承租人而言,立法上赋予其优先购买权却缺乏类似赋予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充分合理性。从立法上的考量上说,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无非是为了稳定一种以债权为纽带所形成的有期限的物的利用关系,以达到保护承租人稳定利用租赁物的目的。这一点通过“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已可实现,也就是说,租赁物的有效利用得到了解决。至于认为承租人基于一定的租赁关系,已在租赁物上形成了稳定的预期,在租赁期满后,继续对其使用或取得所有权是一种有效安排,这并不能构成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有力理由。
首先,承租人是否对租赁物产生依赖本就是一种或然性。虽然在承租人在不需要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时,可以放弃优先购买权,但立法上所规定的三个月期限,足以使出租人丧失许多机会。承租人的这种或然性与共有人对共有物依赖的必然性相比,显然缺少一种必然的保护价值。立法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似乎是出于对承租人的偏爱。
其次,承租人对租赁物形成的依赖,在当代社会极易受市场影响而产生变化。亦即在一个商品交换市场中,承租人取得某项不动产所有权可通过市场来实现,而市场的变动不居也会使承租人原有的依赖基础丧失。因此,法律基于在资源稀缺时代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依赖,来设计资源丰富且高度市场化时代的承租人的需求,已有点不合时宜。而对共有人来说,其优先购买权的基础在于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既有利益,只要共有物存在,共有利益就不会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实实在在地保护了共有人所应享有的现实利益。
再次,从成本和效益角度进行衡量,共有人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赋予也是有差别的。对共有人而言,优先购买权的存在所获得的效益是共有物的完整、稳定的占有和共有物的充分利用,为此支付的代价是第三人同等条件下购买机会的丧失,以及第三人交易风险的承担。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所获得的效益仅是租赁物占有的持续,以及承租人对租赁物可能的继续利用,而为此支付的代价却是出租人处分权的限制、第三人机会的丧失和交易风险的承担。很显然,对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而言,它存在所获得的效益大于成本,而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而言,则其对交易秩序的干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所获得的收益。实际上,即使承租人即使在租赁期间形成了对租赁物的依赖,这种依赖与第三人对租赁物的依赖无异,由于缺少一种物的占有连续性的实在基础,因而并不能构成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强有力的理由。
总而言之,法律上应否设定优先购买权,关键在于立法上是否有必要,在利益衡量上是否行得通。如对于共有人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共存时如何处理,通说认为,前者应优于后者,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物权性的共有关系产生的,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仅是基于债权性的租赁合同产生的,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前者应优于后者。本人对这种通说的结论表示赞同,但对其理由则产生怀疑。应当认为,法律上赋予优先权的初衷并不在于考量权利的逻辑推理,而是考量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结果。如果以权利的效力作为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的亲邻优先权就无法理解,因为在不动产出卖以前,亲邻对出卖人的不动产甚至连债权性的权利都不能享有。如果从物权性的关系角度来考察,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当中,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共有部分都享有共有权,那么为何在商品房出卖时,区分所有人不能享有优先购买权呢?在商品房买卖时,作为共有部分的共有人并不能对抗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所以,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并不能作为是否确定优先购买权或是否优先购买权先行行使的必要依据。当然,一般情况下,优先购买权的顺位基本上不会打破物权、债权效力的位次,这只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物权性的关系的维持与社会效益的增大是一致的,虽然并不一定必然一致。
三 不动产租赁的登记和善意取得
(一)不动产租赁合同的登记问题。
关于承租权优先购买权存在的诸多缺陷,有人提出,不动产租赁合同只有经过登记,承租人才享有优先购买权。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基于对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限制而提出的。就本案而言,依该种说法,只有李某与刘某的租赁合同经过房产部门的登记,刘某才享有优先购买权。本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目前在我国,实际生活房产出租一般并不经过严格的民事登记手续,仍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债权关系。正是由于租赁关系是一种债权关系,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法律才人为地使这种关系物权化,买卖不破租赁其实就是法律人为干预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法律干预的进一步延伸。房产租赁合同如果经过登记,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就是,承租人取得了一种对抗他人的用益物权,在此情形下,买卖不破租赁规则成为多余。但是否承租人的权利表现为一种公示的他物权以后,承租人就当然取得了物权性的优先购买权呢?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依我国法律,房产租赁无论是否经过登记,法律都会赋予其物权的效力,在这一点上并无区别。租赁合同的公示并不能成为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充分条件,正如抵押权的存在不影响抵押物的转让一样。
所以,我认为,租赁合同的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只是租赁关系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不能成为必然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充分条件。
(二)善意第三人保护问题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动产和不动产租赁合同并未经过严格的登记,所以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善意第三人的交易机会会产生冲突。在此情形下,是否应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呢?:“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均没有就第三人为善意的情况下,是否仍适用优先购买权作出规定。一般而言,第三人不会为善意,因为租赁关系很容易知晓。但确实会出现第三人为善意的情况,如本案中,第三人陈某受李某的欺瞒,根本不知道出卖的是已出租的房屋,所以主观上确为善意。在此情形下,如何平衡优先购买权与交易安全就成为法官裁判的核心问题。
首先须明确的是,在本案中,承租人刘某的优先购买权是依法存在的。即使要保护交易安全,这一前提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第三人是善意还是非善意,承租人刘某都有权提起诉讼,,在合同无效这一点上,第三人陈某的善意并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
在此前提下,如果第三人为恶意,那么李某和陈某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在原有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现在的情况是第三人为善意,是否合同无效也会导致登记变更这一法律后果呢?我认为,正如善意取得适用于动产,是作为动产交易安全维护的形式,对不动产而言,也同样适用善意取得的法理。
一般而言,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这是因为,动产以交付获得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转移所有权,而不动产的取得以登记为条件,使不动产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因此不容易发生第三人不知情的所谓的“善意”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绝大多数场合内,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特殊情形下,不动产仍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如在本案中,第三人陈某确为善意,因为承租人刘某优先购买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所有人李某处分权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不是由于原有登记存在瑕疵产生的,而是由于处分权受优先购买权限制这一因素产生的。
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陈某可以直接以公信原则对抗优先购买权,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公信的效力主要在于,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而进行的交易受法律保护。公信力主要是对交易双方和外界产生一种约束力。但本案中,承租人刘某并不是基于对登记效力的信赖,而是对买卖登记本身产生异议,所以公信力不及于刘某。
所以,在本案中,仍宜采用善意取得法理予以保护。李某和陈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但陈某因登记取得合法所有权。
结语
从本案可以看出,不动产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设定在客观上存在许多问题,这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在现代社会,商业租赁已为成经济流转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租赁物的流转速度大大加快。如在日本东京和我国香港地区,在房地产业旺季,每月楼宇所有权交接次数可达几十次,因此在商业租赁中是否一定要保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交易实际情况考虑,出租人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这一规定实际上也是与日益快捷的不动产交易实际情况相违背的。所以,立法上如何限制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需要继续研究的一个问题。其次,在适用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时,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需要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李某于1998年在某市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1999年5月将其出租给刘某,租期二年,2000年7月,由于该商品房所在地段房价猛涨,李某遂将该商品房出卖给陈某,谎称其亲戚在该房暂时居住,并办理了房产转移手续,。刘某得知此事,向李某提出,其为房产承租人,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李某应在出卖房产前三个月通知其本人。李某以时间紧迫,商机不可错失为由予以说明。,,保护其作为承租人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对案例的分析]
本案案情较为简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但在具体适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还在于以本案为例,对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利弊进行分析,进而就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完善提出个人看法。
一、本案中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利弊分析
不动产承租人在不动产动产出卖时,享有优先购买权,是各国立法通例,强化承租人的权利也是近代世界性的立法趋势,租赁权的强化又称之为租赁权的物权化过程。德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明确规定了租赁权的物权效力。日本的建筑物保护法和借地法也将承租人的权利与地上权一样加以保护,承租权和地上权统一被称为“借地权”,作为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34条、第104条、第107条、第124条,以及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15条,也分别规定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和基地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就不动产租赁权物权化以及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设定的立法宗旨来说,不外以下两点:
第一,维护已有的不动产占有与利用关系,避免土地所有与土地利用关系的分离,使已有的不动产利用关系得以延续,以最大限度发挥物的效用;
第二,一般而言,不动产的租赁对于承租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租赁权的物权化可以有效保护承租人的利益,使承租人不因不动产的出卖而遭不利。
就本案而言,承租人刘某如果以租赁的商品房作为当前的安身立命之所,此时在所有人出卖房屋时,刘某享有一定的物权性权利,对于维护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房屋通过市场交易很难取得的情况下,这种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无疑是承租人获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不可多得的途径。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在保护承租人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就本案而言,李某在商品房价格上涨以后,为抓住商机而出卖房屋,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出卖人在三个月前应通知承租人,那么出卖人至少应等待三个月之久,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出卖人坐失商机。
除此之外,我认为,传统立法对承租人赋予优先购买权的立法基础已一定程度上丧失了。
第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赋予的现实环境是不动产资源的匮乏,这一情况在当代得到了改变。在土地和房屋资源异常匮乏的情况下,立法追求的主要是生存和安全价值,是对一种基本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解决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一定程度了促进了这种基本价值的实现。但在现代社会,市场的高度发达,生活资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导致社会形成了一种以市场为媒介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效率成为立法的主要价值目标。对出租人而言,在不动产买卖关系中,如顾及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将可能因此支付巨大的机会成本。这显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效率机制的发挥。而对承租人而言,至少在房产市场里,这种优先购买权的赋予并不能起到保护其基本生活状况的作用,因为承租人也可以顺利从市场取得相应的房产。
第二,从维护既有的房屋利用关系而言,“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即可实现此目的。近现代各国基于对租赁权的保护,使租赁权具有一定的物权效力,在房屋易主后,租赁关系仍继续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既有房屋租赁关系的一种法律保护。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下,既使出租人将房屋出卖,承租人的租赁权仍然存在,并不受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房屋利用关系已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因此,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立法的第一个宗旨而言,租赁房屋的出卖并不会破坏房屋已有的租赁关系。况且租赁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基于合同而形成的债权关系,是有期限的权利。进一步而言,如果优先购买权的赋予是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者是一种稳定的预期的话,那么对于承租人而言,承租期限的维护是其主要目的,至于最后是否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并未包含在其预期之内。所以,从维护房屋利用关系而言,优先购买权并不能对此有实质性的贡献,“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即可实现此目的。
第三,即使在理论上认为,赋予承租人购买权终究可以为承租人在租赁期满后继续利用房屋,但由此支付的成本是巨大的。姑且不说承租人一旦通过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是否还能象在承租期间那样利用房屋,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仅仅从交易安全、公平角度进行利益衡量,结论就非常明显。
近代“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确立是传统民事法律关系规则体系的变奏,在这种规则约束下,租赁物的买卖被人为添加了“租赁关系”这一负担,正是由于这种负担的存在,才使承租人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出租人在出卖房屋时,由于受这种租赁关系的制约,本身已承受一种不利的后果。在一个不动产交易不发达的社会里,对买卖双方增加这一负担,在社会上获得了承租人的预期利益得到保护这一有利结果。但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使交易的快捷、安全至为重要。与此相对应,在一个动态社会中,不动产资源的效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不动产的买卖也不再局限于决策时间长、机会偶然的民事行为,而是表现为带有赢利色彩浓厚的商业行为。在快捷的不动产流动市场中,所有权的交易是受市场控制的,交易双方形式上的公平甚于以往任何时候。这就要求所有权人在处分所有权时,应直接依据市场来决策,不能过多地受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立法上保留“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几乎已达市场所允许的所有人承受负担的阈限,如果还要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则其代价必然是诸多市场交易的无法达成。此时,所损失的就不仅是出卖人可以获得的利益,而是整个市场的安全和效率。
就本案而言,承租人刘某在租赁商品房时,其目的是为了在二年期限内有效地占有和使用该商品房,对于是否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并没有稳定的预期。对于刘某来讲,在承租期内能稳定地占有和利用租赁物,是其现实的利益,法律当然应予维护,但在取得所有权这一问题上,所有权的取得与其租赁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优先购买权的赋予也只是给予承租人优先获得该商品房的所有权而已,这一优先权并没有实质的价值。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关系中,承租人想真正获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只是一种可能而已,租赁关系与买卖关系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如果在立法上想当然地予以确认,那么在保护一种虚幻利益的同时,损失的是众多第三人可能享有的机会和效益。比如,如果本案中承租人是外地打工人员,而买方陈某是房主李某的邻居,那么可以发现,即使留给刘某三个月的考虑时间,刘某也不大可能在此定居,即使其有能力购买房屋,也可在市场顺利获得。而陈某获得这一商品房却可以充分发挥该房屋的区位优势,这正是市场交易所欲达成的效果。但出卖人李某如果在决策时,顾及刘某的优先购买权,那么极有可能错过时机,使一个对双方极为有利的交易无法达成。
所以,应当认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在立法上值得慎重考虑和谨慎选择。
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与共有关系中优先购买权合理性的比较
综观各国立法,在优先购买权的设计上,不外乎三种优先购买权: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和典权人的优先购买权。在优先购买权的立法基础上,却颇不相同,限于篇幅,在于仅比较承租人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几乎是各国民事立法都加以明确规定的。设立此优先购买权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有利于稳定共有关系,维护财产秩序,减少共有人之间的纠纷。第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促进对物的有效率的利用。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共有人优先承购权,旨在防止土地的细分,并兼及消除共有关系,以尽地利。”也就是说,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不但能有效地促进物的利用效率,还能减少原共有人与可能存在的新共有人之间的纠纷。尤其对不动产共有而言,这一点甚为重要。在我国古代,为了促进不动产的有效利用,从北魏时就开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亲邻优先权。唐朝充分继承了此制度,如《唐律》规定,房地产买卖必须先问近亲,次问四邻,近亲四邻不要,才得卖与别人。与共有人的优先权同出一辙,亲邻优先权也是为了充分发挥不动产之经济效益,免除日后可能滋生的斗讼争端,节约社会成本。
由此可见,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的法定化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物的占有和利用秩序的问题,其所获得的社会效益是较大的。当然,从消极影响方面考虑,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以限制共有人的处分权,第三人在同等条件下丧失购买机会为代价的。但必须说明的是,优先购买权的赋予本就是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利益权衡的结果,是对纯粹市场规则的干预,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积极影响相比,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显属次要。
但对承租人而言,立法上赋予其优先购买权却缺乏类似赋予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充分合理性。从立法上的考量上说,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无非是为了稳定一种以债权为纽带所形成的有期限的物的利用关系,以达到保护承租人稳定利用租赁物的目的。这一点通过“买卖不破租赁”规则已可实现,也就是说,租赁物的有效利用得到了解决。至于认为承租人基于一定的租赁关系,已在租赁物上形成了稳定的预期,在租赁期满后,继续对其使用或取得所有权是一种有效安排,这并不能构成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有力理由。
首先,承租人是否对租赁物产生依赖本就是一种或然性。虽然在承租人在不需要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时,可以放弃优先购买权,但立法上所规定的三个月期限,足以使出租人丧失许多机会。承租人的这种或然性与共有人对共有物依赖的必然性相比,显然缺少一种必然的保护价值。立法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似乎是出于对承租人的偏爱。
其次,承租人对租赁物形成的依赖,在当代社会极易受市场影响而产生变化。亦即在一个商品交换市场中,承租人取得某项不动产所有权可通过市场来实现,而市场的变动不居也会使承租人原有的依赖基础丧失。因此,法律基于在资源稀缺时代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依赖,来设计资源丰富且高度市场化时代的承租人的需求,已有点不合时宜。而对共有人来说,其优先购买权的基础在于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既有利益,只要共有物存在,共有利益就不会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实实在在地保护了共有人所应享有的现实利益。
再次,从成本和效益角度进行衡量,共有人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赋予也是有差别的。对共有人而言,优先购买权的存在所获得的效益是共有物的完整、稳定的占有和共有物的充分利用,为此支付的代价是第三人同等条件下购买机会的丧失,以及第三人交易风险的承担。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所获得的效益仅是租赁物占有的持续,以及承租人对租赁物可能的继续利用,而为此支付的代价却是出租人处分权的限制、第三人机会的丧失和交易风险的承担。很显然,对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而言,它存在所获得的效益大于成本,而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而言,则其对交易秩序的干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所获得的收益。实际上,即使承租人即使在租赁期间形成了对租赁物的依赖,这种依赖与第三人对租赁物的依赖无异,由于缺少一种物的占有连续性的实在基础,因而并不能构成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强有力的理由。
总而言之,法律上应否设定优先购买权,关键在于立法上是否有必要,在利益衡量上是否行得通。如对于共有人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共存时如何处理,通说认为,前者应优于后者,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物权性的共有关系产生的,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仅是基于债权性的租赁合同产生的,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前者应优于后者。本人对这种通说的结论表示赞同,但对其理由则产生怀疑。应当认为,法律上赋予优先权的初衷并不在于考量权利的逻辑推理,而是考量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结果。如果以权利的效力作为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的亲邻优先权就无法理解,因为在不动产出卖以前,亲邻对出卖人的不动产甚至连债权性的权利都不能享有。如果从物权性的关系角度来考察,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当中,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共有部分都享有共有权,那么为何在商品房出卖时,区分所有人不能享有优先购买权呢?在商品房买卖时,作为共有部分的共有人并不能对抗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所以,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并不能作为是否确定优先购买权或是否优先购买权先行行使的必要依据。当然,一般情况下,优先购买权的顺位基本上不会打破物权、债权效力的位次,这只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物权性的关系的维持与社会效益的增大是一致的,虽然并不一定必然一致。
三 不动产租赁的登记和善意取得
(一)不动产租赁合同的登记问题。
关于承租权优先购买权存在的诸多缺陷,有人提出,不动产租赁合同只有经过登记,承租人才享有优先购买权。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基于对不动产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限制而提出的。就本案而言,依该种说法,只有李某与刘某的租赁合同经过房产部门的登记,刘某才享有优先购买权。本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目前在我国,实际生活房产出租一般并不经过严格的民事登记手续,仍表现为一种松散的债权关系。正是由于租赁关系是一种债权关系,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法律才人为地使这种关系物权化,买卖不破租赁其实就是法律人为干预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法律干预的进一步延伸。房产租赁合同如果经过登记,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就是,承租人取得了一种对抗他人的用益物权,在此情形下,买卖不破租赁规则成为多余。但是否承租人的权利表现为一种公示的他物权以后,承租人就当然取得了物权性的优先购买权呢?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依我国法律,房产租赁无论是否经过登记,法律都会赋予其物权的效力,在这一点上并无区别。租赁合同的公示并不能成为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充分条件,正如抵押权的存在不影响抵押物的转让一样。
所以,我认为,租赁合同的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只是租赁关系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不能成为必然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充分条件。
(二)善意第三人保护问题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动产和不动产租赁合同并未经过严格的登记,所以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善意第三人的交易机会会产生冲突。在此情形下,是否应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呢?:“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均没有就第三人为善意的情况下,是否仍适用优先购买权作出规定。一般而言,第三人不会为善意,因为租赁关系很容易知晓。但确实会出现第三人为善意的情况,如本案中,第三人陈某受李某的欺瞒,根本不知道出卖的是已出租的房屋,所以主观上确为善意。在此情形下,如何平衡优先购买权与交易安全就成为法官裁判的核心问题。
首先须明确的是,在本案中,承租人刘某的优先购买权是依法存在的。即使要保护交易安全,这一前提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第三人是善意还是非善意,承租人刘某都有权提起诉讼,,在合同无效这一点上,第三人陈某的善意并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
在此前提下,如果第三人为恶意,那么李某和陈某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在原有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现在的情况是第三人为善意,是否合同无效也会导致登记变更这一法律后果呢?我认为,正如善意取得适用于动产,是作为动产交易安全维护的形式,对不动产而言,也同样适用善意取得的法理。
一般而言,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动产。这是因为,动产以交付获得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转移所有权,而不动产的取得以登记为条件,使不动产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因此不容易发生第三人不知情的所谓的“善意”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绝大多数场合内,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特殊情形下,不动产仍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如在本案中,第三人陈某确为善意,因为承租人刘某优先购买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所有人李某处分权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不是由于原有登记存在瑕疵产生的,而是由于处分权受优先购买权限制这一因素产生的。
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陈某可以直接以公信原则对抗优先购买权,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公信的效力主要在于,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而进行的交易受法律保护。公信力主要是对交易双方和外界产生一种约束力。但本案中,承租人刘某并不是基于对登记效力的信赖,而是对买卖登记本身产生异议,所以公信力不及于刘某。
所以,在本案中,仍宜采用善意取得法理予以保护。李某和陈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但陈某因登记取得合法所有权。
结语
从本案可以看出,不动产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设定在客观上存在许多问题,这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在现代社会,商业租赁已为成经济流转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租赁物的流转速度大大加快。如在日本东京和我国香港地区,在房地产业旺季,每月楼宇所有权交接次数可达几十次,因此在商业租赁中是否一定要保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交易实际情况考虑,出租人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这一规定实际上也是与日益快捷的不动产交易实际情况相违背的。所以,立法上如何限制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需要继续研究的一个问题。其次,在适用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时,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需要在法律上予以确认。
最新资讯
-
06-13 0
-
01-20 2
-
08-04 1
-
08-20 0
-
08-25 1
-
08-03 1